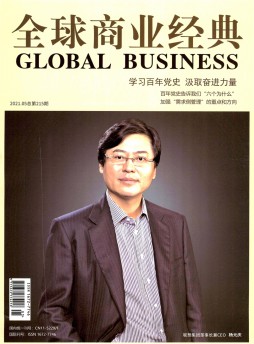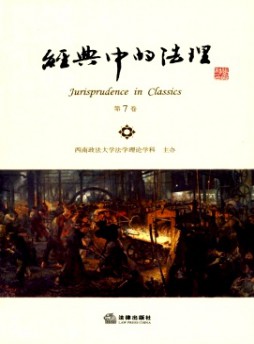經(jīng)典哲學(xué)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shù)篇優(yōu)質(zhì)經(jīng)典哲學(xué)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lái)啟發(fā),助您在寫(xiě)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2] 理解就是此在在理解的前結(jié)構(gòu)的基礎(chǔ)上對(duì)未來(lái)進(jìn)行的籌劃。從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理解的前結(jié)構(gòu)決定了理解,甚至可以說(shuō)理解是理解的前結(jié)構(gòu)的“重復(fù)”。
[12] 這些多樣化的形態(tài)之間可能形成互補(bǔ)的關(guān)系,也可能形成競(jìng)爭(zhēng)的關(guān)系。解釋文本的文本又形成新的文本,我們稱之為衍生文本。被解釋的原初文本與解釋文本而形成的衍生文本之間的關(guān)系,是源與流、一與多的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并不是簡(jiǎn)單的派生與被派生的關(guān)系,而是一種循環(huán)關(guān)系。一方面,文本及其意義存在于對(duì)它的解釋中,“多”和“流”是對(duì)“一”和“源”的補(bǔ)充和發(fā)展(當(dāng)然也包括偏離),現(xiàn)實(shí)中只能通過(guò)“多”和“流”去達(dá)到“一”和“源”,這是解釋對(duì)文本意義的制約性;另一方面,文本又制約著對(duì)它的解釋,并且為評(píng)價(jià)各種解釋提供某種尺度和準(zhǔn)繩,當(dāng)然,這種評(píng)價(jià)是通過(guò)各種解釋之間的比較和競(jìng)爭(zhēng)來(lái)實(shí)現(xiàn)的。
[15]
第2篇
中國(guó)哲學(xué)史上的“言意之辨”肇端于中國(guó)哲學(xué)原創(chuàng)建構(gòu)的先秦時(shí)期,既是中國(guó)哲學(xué)或哲學(xué)史的中心論題,同時(shí)也是中國(guó)哲學(xué)原創(chuàng)建構(gòu)的理論和方法。魏晉“言意之辨”以經(jīng)典文本的意義追尋和終極價(jià)值的哲學(xué)建構(gòu)為旨?xì)w,既是對(duì)兩漢經(jīng)學(xué)賴以存在和發(fā)展的兩大基石——“言盡意”論和“象盡意”論——及其經(jīng)典詮釋方法的解構(gòu)和顛覆,同時(shí)也是對(duì)先秦時(shí)期“言意之辨”的理論和方法的繼承和發(fā)展。它既不是玄學(xué)家發(fā)現(xiàn)的“新眼光”,也不是玄學(xué)家用于本體論哲學(xué)體系建構(gòu)的“新方法”。“言意之辨”在魏晉時(shí)期的重新興起,以“言(象)外之意”的發(fā)現(xiàn)和“言(象)不盡意論”的重新提出為濫觴,不是“言意之辨蓋起于識(shí)鑒”,而是人物“識(shí)鑒”有賴于“言意之辨”,而這恰恰也正是魏晉“言意之辨”的實(shí)質(zhì)、意義和價(jià)值所在。
【關(guān)鍵詞】 魏晉玄學(xué)/言意之辨/經(jīng)典文本/終極價(jià)值
魏晉時(shí)期是中國(guó)哲學(xué)史上的“言意之辨”的鼎盛時(shí)期,而魏晉“言意之辨”的概念,則是由湯用彤先生于1942年首先提出來(lái)的[1] (P. 240)。按照湯用彤先生的觀點(diǎn),魏晉“言意之辨實(shí)亦起于漢魏間之名學(xué)”,而“名理之學(xué)源于評(píng)論人物”,“故言意之辨蓋起于識(shí)鑒”[2] (P. 24)。然而,進(jìn)一步的研究表明,中國(guó)哲學(xué)史上的“言意之辨”肇端于中國(guó)哲學(xué)原創(chuàng)建構(gòu)的先秦時(shí)期,既是中國(guó)哲學(xué)或哲學(xué)史的中心論題,同時(shí)也是中國(guó)哲學(xué)原創(chuàng)建構(gòu)的理論和方法。它既不是玄學(xué)家發(fā)現(xiàn)的“新眼光”,也不是玄學(xué)家用于本體論哲學(xué)體系建構(gòu)的“新方法”。魏晉“言意之辨”以經(jīng)典文本的意義追尋和終極價(jià)值的哲學(xué)建構(gòu)為旨?xì)w,既是對(duì)兩漢經(jīng)學(xué)賴以存在和發(fā)展的兩大基石——“言盡意”論和“象盡意”論——及其經(jīng)典詮釋方法的解構(gòu)和顛覆,同時(shí)也是對(duì)先秦時(shí)期“言意之辨”的理論和方法的繼承和發(fā)展。“言意之辨”在魏晉時(shí)期的重新興起,以“言(象)外之意”的發(fā)現(xiàn)和“言(象)不盡意論”的重新提出為濫觴,不是“言意之辨蓋起于識(shí)鑒”,而是人物“識(shí)鑒”有賴于“言意之辨”。
一
從現(xiàn)代哲學(xué)的視域看,中國(guó)哲學(xué)史上的“言意之辨”肇端于中國(guó)哲學(xué)原創(chuàng)性建構(gòu)的先秦時(shí)期或中國(guó)“哲學(xué)的突破”期,以“天人合一”的“文化生態(tài)模式”為背景,以社會(huì)治亂和終極關(guān)切為旨?xì)w,既緣起于“所行之道”或“生生之道”,向著為形上本體之“道”的理性升華及其語(yǔ)言的表達(dá),又緣起于《易傳》作者對(duì)《周易》文本的哲學(xué)解釋,并集中體現(xiàn)在兩個(gè)問(wèn)題上:其一是人類語(yǔ)言能否完全表達(dá)體認(rèn)主體對(duì)本體存在之“道”的體認(rèn)以及究竟應(yīng)當(dāng)如何表達(dá)主體對(duì)本體之“道”的理解和認(rèn)識(shí)的問(wèn)題;其二是《周易》文本中的“言”、“象”、“數(shù)”符號(hào)系統(tǒng)是否完全表達(dá)了圣人之意,通過(guò)《周易》“言”、“象”、“數(shù)”符號(hào)系統(tǒng)能否可以完全理解和把握圣人之意的問(wèn)題。可以說(shuō),這兩個(gè)問(wèn)題既是中國(guó)哲學(xué)的初始問(wèn)題,也是中國(guó)哲學(xué)的中心論題和先秦諸子的“言意之辨”經(jīng)過(guò)“兩漢諸儒的宗經(jīng)正緯”在魏晉時(shí)期重新興起的思想基礎(chǔ)、理論來(lái)源和深層原因。
“道”是老子哲學(xué)乃至中國(guó)哲學(xué)的最高本體范疇。而如果說(shuō)中國(guó)“哲學(xué)的突破”以“道”作為哲學(xué)本體論范疇的提出為標(biāo)志的話,那么老子則不僅是“道”本體論哲學(xué)的創(chuàng)立者或中國(guó)哲學(xué)的開(kāi)創(chuàng)者,而且同時(shí)也是從“道”的形而上的層面上“非言”的第一人。而當(dāng)老子作為本體存在之“道”的體認(rèn)主體和言說(shuō)主體同時(shí)出現(xiàn)時(shí),即在他不得不提出和表達(dá)自己對(duì)“道”的體認(rèn)時(shí),首當(dāng)其沖的問(wèn)題便是,能否言說(shuō)和究竟應(yīng)當(dāng)如何言說(shuō)的問(wèn)題。而當(dāng)他試圖對(duì)“道”進(jìn)行言說(shuō)時(shí),便發(fā)現(xiàn)了這樣一個(gè)基本事實(shí):在本體存在之“道”與人類語(yǔ)言之間,實(shí)際上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這就是著名的“言道悖論”。
《老子》開(kāi)宗明義便說(shu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說(shu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dú)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二十五章)在老子看來(lái),“道”雖“可道”,但言說(shuō)出來(lái)的“道”已不是心中的那個(gè)“道”或本來(lái)意義上的“道”;“道”雖可名之為“道”,但可名的“道”也已不是心中的那個(gè)“道”或本來(lái)意義上的“道”。而“道”之所以不可言說(shuō),不可以名之,首先是因?yàn)椤暗馈笔翘斓厝f(wàn)物存在的根據(jù)、本質(zhì)和本體。其次是因?yàn)椋懊笔窍鄬?duì)于“實(shí)”而言的,“道”既非“有”,又非“實(shí)”,當(dāng)然,不可以“名”舉之。而依照“物固有形,形固有名”的命名標(biāo)準(zhǔn),故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說(shuō)法和“尋尋呵,不可名也”的感嘆。
當(dāng)然,這并不是要放棄一切形式的言說(shuō)。事實(shí)上,當(dāng)老子在說(shuō)“道可道,非常道”時(shí),本身就是在言說(shuō)那本不可言說(shuō)的“道”。不過(guò),在老子看來(lái),言說(shuō)出來(lái)的“道”,已經(jīng)不是心目中的“道”,或本然“存在”的“道”了。“道出言,淡無(wú)味,視不可見(jiàn),聽(tīng)不足聞,用不可既。”(《老子》三十五章)可見(jiàn),問(wèn)題的關(guān)鍵并不在于要不要言說(shuō)和能不能言說(shuō),而在于究竟應(yīng)當(dāng)以何種方式言說(shuō)才能使其得以本然的呈現(xiàn)的問(wèn)題。
綜觀《老子》文本,其所推崇的言道方式主要有二:其一是“行”的方式。其作為最高境界的言說(shuō)方式,就在于它凝聚了體認(rèn)主體對(duì)“道”的全部體悟和理解。“是故圣人處無(wú)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二章)“不言之教,無(wú)為之益,天下希及之。”(《老子》四十章)其二是“反”的方式。老子說(shuō):“正言若反。”(《老子》七十八章)“大曰逝,逝曰遠(yuǎn),遠(yuǎn)曰反。”(《老子》二十五章)所謂“反”,就是“復(fù)命”、“歸根”、“復(fù)歸于樸”(《老子》二十八章)。只有“反”才能超越外物的遮蔽和語(yǔ)言的界限,回歸本然、本真之“道”,以實(shí)現(xiàn)對(duì)本然、本真、本體之“道”的整體性把握。而如果要?dú)w結(jié)到一點(diǎn),那就是“不言”。而“不言”的實(shí)質(zhì),就是要以“行”為“言”,以“反”代“知”,超越外物和語(yǔ)言對(duì)“道”的遮蔽,以達(dá)到對(duì)本然、本真、本體之“道”的整體性的表達(dá)、理解和把握的思維境界。
正是從“言道悖論”這一中國(guó)哲學(xué)的初始問(wèn)題和理論難題出發(fā),而有莊子“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jiàn),見(jiàn)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dāng)名”的宏論和“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的“言不盡意”論的提出,以及“得意忘言”的方法論對(duì)“言道悖論”的超越和對(duì)以儒、墨、名、法諸家為代表的知識(shí)論和邏輯學(xué)理論和方法——“言盡意論”的解構(gòu)和顛覆。
就此而論,莊子的理論貢獻(xiàn)主要有二:一是從本體論的理論視角對(duì)“道”與“物”關(guān)系作了明確地區(qū)分,并設(shè)定了人類知識(shí)的界限。他說(shuō):“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莊子·則陽(yáng)》)而“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莊子·應(yīng)帝王》)而“物物者,非物。”“物物者與物無(wú)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莊子·知北游》)所以,在莊子看來(lái),“道”,不僅不是一個(gè)言說(shuō)的對(duì)象,而且正是它構(gòu)成了人類知識(shí)的界限。二是從經(jīng)典詮釋學(xué)的理論視角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得意忘言”的理論和方法。“得意忘言”以“言不盡意”為基礎(chǔ),既是對(duì)“言道悖論”的理性超越,更是對(duì)以名實(shí)關(guān)系的概念論為基礎(chǔ)的“言盡意論”的解構(gòu)和顛覆。
正是以老子、莊子及其道家的“道論”和“言不盡意論”立論,《易傳》作者則不僅明確提出了“言不盡意”和“圣人立象以盡意”的思想和命題,而且造就了中國(guó)哲學(xué)特有的注重類比和義理性的“意象”思維的哲學(xué)傳統(tǒng)。《易傳·系辭上》云:“書(shū)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圣人之意其不可見(jiàn)乎?是故圣人立象以盡意,設(shè)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也就是說(shuō),圣人之所以要“立象以盡意,設(shè)卦以盡情偽”,就是因?yàn)椤把圆槐M意”,而“言”之所以不能“盡意”,就是因?yàn)椋@里所謂的“意”,既是圣人之“意”,也是天地之意,是天地之理,是“天人合一”之“意”,是人合于天之“意”,人文創(chuàng)造之“意”,是意義生成之“意”,是理想境界之“意”,是文化創(chuàng)造的原動(dòng)力,是元文化之源。如此無(wú)限延伸、生生不已的天人之理,非語(yǔ)言文字所能容納和承載。而圣人之所以要“立象以盡意”,在《易傳》作者看來(lái),除“言不盡意”的原因外,最根本的就是因?yàn)椋跋蟆本哂袩o(wú)限大的容量,可以容納和承載那說(shuō)不完道不盡的“道”和“意”;就是因?yàn)樗从凇白匀弧薄⒛M“自然”,是那生氣勃勃的“自然”之“象”[3]。
《系辭上》云:“圣人有以見(jiàn)天下之,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系辭下》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niǎo)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yuǎn)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wàn)物之情。”《系辭下》又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所以,“象”是萬(wàn)物之“象”,是人文之“象”,是整體之“象”,是系統(tǒng)之“象”,是運(yùn)動(dòng)變化之“象”,是萬(wàn)物和諧存在之“象”,是圣人之“意”的表達(dá),也是“天地之道”的詩(shī)意表達(dá)。但需要指出的是,“立象以盡意”與“象盡意”有別。“象盡意”強(qiáng)調(diào)的是“象”與“意”之間的完全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而“立象以盡意”以“言不盡意”為基礎(chǔ),其作為《易傳》作者對(duì)《易經(jīng)》“言”、“象”、“意”之關(guān)系的一種解釋,則主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圣人“立象”的目的是為了“盡意”,至于“象”能否盡“意”,《易傳》的作者并沒(méi)有說(shuō)。沒(méi)有說(shuō),當(dāng)然并不等于沒(méi)有問(wèn)題。
問(wèn)題就在于,它不僅蘊(yùn)含了“言”、“象”與“意”之間的關(guān)系問(wèn)題,而且以“言不盡意”為基礎(chǔ),同時(shí)蘊(yùn)含了三種可能的理解和方向。其一是“象(言)盡意”論;其二是“象(言)不盡意”論;其三是“得意忘言(象)”論。如果說(shuō),以“象(言)盡意”論為基礎(chǔ),而有兩漢經(jīng)學(xué)及其方法論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那么,“象(言)不盡意”在漢魏之際的重新發(fā)現(xiàn)、提出和討論,則正是魏晉“言意之辨”之所以發(fā)生的深層原因。
二
魏晉“言意之辨”肇端于漢魏之際,以經(jīng)典文本的意義追尋和終極價(jià)值的哲學(xué)建構(gòu)為旨?xì)w,而以“言(象)不盡意”在漢魏之際的重新發(fā)現(xiàn)、提出和討論為濫觴,既是對(duì)先期“言意之辨”的繼承和發(fā)展,同時(shí)又是對(duì)兩漢經(jīng)學(xué)賴以存在和發(fā)展的“言(象)盡意”論的理論和方法的解構(gòu)和顛覆。
先秦以后,經(jīng)學(xué)繁盛,故有漢代經(jīng)學(xué)中的“章句之學(xué)”和“象數(shù)之學(xué)”的興起。“章句之學(xué)”源于荀學(xué),亦可追溯自墨家經(jīng)學(xué),以名實(shí)關(guān)系的概念論或“形名之學(xué)”的“言盡意論”為基礎(chǔ),所以最重“師法”。“師之所傳,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師說(shuō)即不用。”[4] (P. 136)以后逐漸演化為一種繁瑣哲學(xué)。不僅繁瑣、荒誕,而且遮蔽了儒家關(guān)于“性與天道”問(wèn)題的形上學(xué)思考。正如此,王弼所說(shuō):“夫立言垂教,將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傳辭,將以正邪,而勢(shì)至于繁。既求道中,不可勝御,是以修本廢言,則天而行化。”不僅深刻揭示了圣人“立言垂教,將以通性”的根本目的,而且針對(duì)經(jīng)學(xué)舍本逐末“而勢(shì)至于繁”的弊端,從而明確提出了“修本廢言,則天下行化”的主張,不僅振聾發(fā)聵,而且直接引發(fā)了魏晉時(shí)期的“言意之辨”。
而晉人張韓則作《不用舌論》,并引“天何言哉”為論據(jù),亦述重“意”輕“言”和“不言”之說(shuō)而趨向于整體把握和直覺(jué)體認(rèn)。他說(shuō):“余以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徒知無(wú)舌之通心,未盡有舌之必(疑本“不”字)通心也。仲尼云:‘天何言哉,四時(shí)行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可以說(shuō),“性與天道”問(wèn)題的重新提出和在這個(gè)問(wèn)題上的“言意之辨”,既是對(duì)儒家經(jīng)典的神圣性的顛覆和經(jīng)學(xué)方法的解構(gòu),也是魏晉“言意之辨”重新興起的重要原因。
而兩漢“象數(shù)之學(xué)”以《易傳》之“立象盡意”論立論,主要以孟喜、京房,及《易緯》為代表。關(guān)于解釋《周易》的原則與方法,孟、京提出了兩個(gè)觀點(diǎn):一是主張以奇偶之?dāng)?shù)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來(lái)解釋《周易》經(jīng)傳;二是主張以“卦氣說(shuō)”解釋《周易》原理。前者反映出漢代易學(xué)的根本特點(diǎn)是采用了“象數(shù)學(xué)”的研究方法。后者詮釋原則的提出則與漢代流行的“陰陽(yáng)五行說(shuō)”及“今文經(jīng)學(xué)”有關(guān)。“陰陽(yáng)五行說(shuō)”強(qiáng)調(diào)陰陽(yáng)二氣的運(yùn)行及五行生克對(duì)社會(huì)人事的影響;“今文經(jīng)學(xué)”則在天人之間作牽強(qiáng)附會(huì)的溝通,而當(dāng)時(shí)易學(xué)中的“卦氣說(shuō)”恰恰是在八卦、八十四卦的原理與陰陽(yáng)二氣的運(yùn)行及五行生克之道之間劃了等號(hào),這使西漢易學(xué)同樣打上了時(shí)代烙印而與《周易》本義有很大距離。至東漢時(shí),這種“象數(shù)學(xué)”與“卦氣說(shuō)”相結(jié)合的詮釋方法演變?yōu)橐环N數(shù)字游戲并最終引出了玄學(xué)家的否定[5] 和漢魏之際以《周易》為核心的“言”、“象”、“意”關(guān)系問(wèn)題的提出和討論。
需要指出的是,兩漢經(jīng)學(xué)以“言盡意論”和“立象盡意論”立論,固然具有其思想的合理性和深刻的社會(huì)歷史原因,然而,其“究心”于“系表之言”和“象”內(nèi)之“意”,只在語(yǔ)言文字上討意度,而忽視對(duì)“性與天道”或“道”一類抽象本體的形上追思,實(shí)際上是對(duì)先秦“言意之辨”的思想主題和內(nèi)在精神的嚴(yán)重背離。而這種背離的嚴(yán)重性正在于它從根本上導(dǎo)致了終極價(jià)值的缺失和社會(huì)秩序的失范,而這也正是玄學(xué)家倚重“道”、“玄”而“究心抽象原理”的深層原因。而當(dāng)玄學(xué)家以價(jià)值重建為己任而“究心”于終極價(jià)值——“性與天道”或“道”——一類的抽象本體的哲學(xué)建構(gòu)之時(shí),故有經(jīng)典文本的意義追尋和價(jià)值重建以及先秦“言意之辨”的重新繼起。而魏晉“言意之辨”的興起,則既是對(duì)先秦“言意之辨”的承繼和發(fā)展,又是對(duì)兩漢經(jīng)學(xué)賴以立論的“言(象)盡意”論的理論和方法的解構(gòu)和顛覆。而兩漢經(jīng)學(xué)及其方法的極端化發(fā)展,則不僅為“言意之辨”在魏晉時(shí)期的重新討論和再度展開(kāi)提供了直接而深刻的學(xué)術(shù)背景,而且為“言意之辨”在魏晉時(shí)期的重新討論和再度展開(kāi)提供了一個(gè)強(qiáng)大的動(dòng)力機(jī)制。可以說(shuō),魏晉“言意之辨”的發(fā)生、發(fā)展,正是兩漢經(jīng)學(xué)及其方法的極端化發(fā)展的必然產(chǎn)物。
魏晉“言意之辨”肇端于漢魏之際,既以兩漢經(jīng)學(xué)及其方法的極端化發(fā)展為基礎(chǔ),又以“言(象)不盡意”論的重新提出為濫觴。而魏晉時(shí)期“言不盡意”論的首倡者,正是“獨(dú)好言道”的魏人荀粲。可以說(shuō),“以儒術(shù)論議”的荀氏家族,因?qū)?jīng)典文本的理解不同而有“言意之辨”,其作為魏晉“言意之辨”發(fā)生的一個(gè)縮影,無(wú)疑為我們進(jìn)一步深刻揭示魏晉“言意之辨”緣起之謎提供了具體的分析路徑和重要的思想史信息。
據(jù)《三國(guó)志·魏書(shū)·荀彧傳》,裴松之注引《晉陽(yáng)秋》載何劭《荀粲傳》云:“粲諸兄并以儒術(shù)論議,而粲獨(dú)好言道,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然則六籍雖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俁難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盡意,系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為不可得而聞見(jiàn)哉?’粲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象)外者也;系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蘊(yùn)而不出矣。’及當(dāng)時(shí)能言者不能屈也。”從現(xiàn)有文獻(xiàn)資料來(lái)看,荀氏家族的“言意之辨”是先秦以后和魏晉以前有關(guān)“言意之辨”的最早和最集中的記錄。而從這段記述性文字的思想內(nèi)容來(lái)看,其所討論的問(wèn)題依然是主體、語(yǔ)言(包括“象”)和存在即“性與天道”和“圣人之意”的關(guān)系問(wèn)題,并具體體現(xiàn)在對(duì)前述儒家兩個(gè)經(jīng)典性元命題的理解上。其一是對(duì)“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的理解問(wèn)題;其二是對(duì)《易傳》“言不盡意”和“立象以盡意”兩個(gè)命題及其關(guān)系的理解問(wèn)題。以粲兄俁為代表的傳統(tǒng)觀點(diǎn)認(rèn)為,《易傳·系辭上》所言“立象以盡意”,即“立象”能夠“盡意”。
正如王夫之所說(shuō):“天下無(wú)象外之道,何也?有外則相與為兩,即甚親而亦如父之于子也。無(wú)外則相與為一,雖有異名,而亦若耳目之于聰明也。”(《周易外傳》卷六)強(qiáng)調(diào)的是“言”、“象”與“意”之間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而這也正是“言盡意”論者的思想特點(diǎn)和理論根據(jù)。然而,在荀粲看來(lái),既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所以“六籍雖存,固圣人之糠秕”。《易》之“意”是即“圣人之意”,是圣人對(duì)“天地之道”的感悟和體驗(yàn);而《易》之“象”,則為“物象”,而“物象”是所無(wú)法容納和承載“圣人之意”的。所以通過(guò)《易》之“言”、“象”符號(hào)系統(tǒng)也是無(wú)法完全理解和把握“圣人之意”的。因此,“立象以盡意”只能盡“象”內(nèi)之“意”,而不能盡“象外之意”。
正如管輅所說(shuō):“夫物(按:即物象),不精不為神,數(shù)不妙不為術(shù),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孔子曰:‘書(shū)不盡言’,言之細(xì)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魏志·方技傳》注引《輅別傳》)而這也正是荀粲以“六籍”為“圣人之糠秕”,而主張“言(象)不盡意”的理論根據(jù)。所以,綜觀荀氏家族的辯論,以“言(象)不盡意論”的重新提出為濫觴,以經(jīng)典文本的意義,即“圣人之意”的形上追尋為旨?xì)w,既是對(duì)先秦“言意之辨”的繼承和發(fā)展,也是對(duì)兩漢經(jīng)學(xué)賴以存在和發(fā)展的“言盡意”的理論和方法的顛覆和解構(gòu)。因而這里主要涉及兩個(gè)問(wèn)題:其一,“六籍”是否完全表達(dá)了圣人關(guān)于“性與天道”的思想,通過(guò)“六籍”能否完全把握圣人關(guān)于“言性與天道”的思想;其二,“立象”能否“盡意”,通過(guò)“觀象”能否完全把握“圣人之意”。而依據(jù)各自對(duì)這兩個(gè)問(wèn)題的不同回答,故有最初的“盡意”與“不盡意”之說(shuō)和“言意之辨”。然而,這兩個(gè)問(wèn)題的進(jìn)一步討論又必然涉及兩個(gè)更深層次的問(wèn)題:其一是基于“盡意”和“不盡意”的內(nèi)在矛盾,而有如何對(duì)待圣人之“言”和《周易》之“象”的問(wèn)題;其二是“道”與“有”、“無(wú)”的關(guān)系問(wèn)題。如果說(shuō)前者涉及兩漢經(jīng)學(xué)及其方法論的合法性問(wèn)題,那么后者則是荀氏兄弟留給后世哲學(xué)的根本性問(wèn)題。而這兩個(gè)問(wèn)題的最終解決,顯然有賴于老莊道家言意思想的引入,而這也正是道家思想之所以能夠成為玄學(xué)家用于解構(gòu)經(jīng)學(xué)和創(chuàng)建玄學(xué)本體論哲學(xué)體系的理論和方法的深層原因。而站在儒家的立場(chǎng)對(duì)這兩個(gè)問(wèn)題作出全面系統(tǒng)論述的正是“正始玄風(fēng)”的開(kāi)創(chuàng)者何晏和王弼。
何晏廣集兩漢“論語(yǔ)學(xué)”諸家之大成,以“無(wú)”釋“道”,繼往開(kāi)來(lái),不僅凸顯了《論語(yǔ)》的形上學(xué)意義,而且創(chuàng)立了一種自然、生命的本體論,而這個(gè)本體就是“無(wú)”。而如果說(shuō)何晏以道家思想詮釋儒家思想,開(kāi)創(chuàng)了玄學(xué)化的新經(jīng)學(xué)的話,那么作為“正始玄學(xué)最強(qiáng)音”的王弼,則更主張“以無(wú)為本”,“執(zhí)一統(tǒng)眾”,從而不僅實(shí)現(xiàn)了儒道思想的會(huì)通,而且將儒學(xué)真正推向了玄學(xué)本體論哲學(xué)建構(gòu)的新階段。正是從“無(wú)”的本體論出發(fā),他不僅在《老子指略》中對(duì)“言不盡意”進(jìn)行了具體而深入的論證,而且在《周易略例》中對(duì)莊子“得意忘言”的理論和方法作了全面而系統(tǒng)的闡發(fā)。何晏、王弼主張“以無(wú)為本”,而郭象“崇有”,則主張“獨(dú)化”于“玄冥之境”。而所謂玄冥之境,正是由魏晉“言意之辨”所開(kāi)出的生命境界和思維境界。
三
應(yīng)當(dāng)承認(rèn),魏晉“言意之辨”的興起,以荀粲“言(象)不盡意”論的重新提出為濫觴,有其深刻的社會(huì)歷史原因。漢魏之際“人物多擬偽”也是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但這并不意味著“品評(píng)人物”和“名理之學(xué)”的興起就是魏晉“言意之辨”發(fā)生的直接誘因。事實(shí)上,無(wú)論是先秦時(shí)期的“言意之辨”還是魏晉時(shí)期的“言意之辨”的興起都是以“言不盡意”論的提出為標(biāo)志,而后有“言盡意論”對(duì)“言不盡意論”的詰難和主體、語(yǔ)言和存在關(guān)系問(wèn)題上的“言意之辨”。不是“言意之辨蓋起于識(shí)鑒”,而是人物“識(shí)鑒”有賴于“言意之辨”,而這恰恰也正是魏晉“言意之辨”的實(shí)質(zhì)、意義和價(jià)值所在。
魏晉“言意之辨”的興起,以荀粲“言不盡意”論的提出為濫觴,首先是被視為異端而存在的。而異端相對(duì)于傳統(tǒng)、正統(tǒng)而言,其主要是“言盡意”的觀點(diǎn)。所以“言盡意”論者又有“違眾先生”之稱。而荀氏兄弟之間的“言意之辨”作為魏晉“言意之辯”的最早記錄,從時(shí)間上看當(dāng)在漢魏之際的太和年間。而這一時(shí)期也正是兩漢經(jīng)學(xué)轉(zhuǎn)向魏晉玄學(xué)的重要時(shí)期。其中一個(gè)重要的特點(diǎn)是因談?wù)摗安判浴焙汀捌吩u(píng)人物”而有“名理之學(xué)”的興起。因?yàn)椤白R(shí)鑒”和“品評(píng)”人物要有一定的名目和準(zhǔn)則,而這些名目和準(zhǔn)則,在當(dāng)時(shí)就叫做“名理”。魏晉“名理”,分“才性之名理”和“志識(shí)之名理”。就其思想理論淵源而言,多與儒家的“正名”理論和“心性之學(xué)”乃至法家的“形(刑)名之學(xué)”的概念論有著較為密切的關(guān)系。然而,從思想內(nèi)容上看,“名理之學(xué)”“源于評(píng)論人物”,多以“形名之學(xué)”的概念論為基礎(chǔ),不僅主要體現(xiàn)在“察舉”取士和人物“才性”方面,而且多與“言盡意論”相聯(lián)系,雖然最終要涉及“自然”與“名教”的關(guān)系問(wèn)題,即理想人格和終極價(jià)值問(wèn)題,但從“言意之辨”的起源來(lái)看,則多以名實(shí)關(guān)系的概念論為基礎(chǔ),而與“言不盡意論”的提出并無(wú)直接的關(guān)聯(lián)。而“名理之學(xué)”以先秦以來(lái)的“形名之學(xué)”的概念論為基礎(chǔ),多與“言盡意論”相聯(lián)系,不僅不是“言不盡意論”的理論根據(jù),相反正是“言盡意論”反對(duì)“言不盡意論”的強(qiáng)大思想武器。所以,說(shuō)魏晉“言意之辨”緣起于“人物識(shí)鑒”,顯然是缺乏根據(jù)的。
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還可以從荀粲等人談?wù)摰膬?nèi)容和語(yǔ)境中得到進(jìn)一步證明。據(jù)《世說(shuō)新語(yǔ)·文學(xué)》載:“傅嘏善言虛盛,荀粲談尚玄遠(yuǎn)。每至共語(yǔ),有爭(zhēng)而不相喻。裴冀州(徽)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情,常使兩情相得,彼此俱暢。”“是時(shí)何晏以才辯顯于貴戚之間。鄧飆好變通,和徒黨,名于閭閻。而夏侯玄以責(zé)臣子,少有重名,為之宗主。求交于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shí)遠(yuǎn)心,然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世之杰,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能,非國(guó)之利。”另?yè)?jù)《三國(guó)志·魏書(shū)·荀彧傳》注引何劭《荀粲傳》云,荀粲在家與諸兄論辯之后,于太和初年(227年)到京邑與傅嘏談。而《三國(guó)志·魏書(shū)·傅嘏傳》謂:“嘏常論才性同異,鐘會(huì)集而論之。”《藝文類聚》十九載晉歐陽(yáng)建《言盡意論》說(shuō):“世之論者以為‘言不盡意’,由來(lái)尚矣。至乎通才達(dá)識(shí)咸以為然。若夫蔣公之論眸子,鐘、傅之言才性,莫不引為談證。”以至于主張“言盡意”的歐陽(yáng)建,在論證“言盡意”的過(guò)程中,同樣也透露出了“言不盡意”的思想。其文曰:“夫天不言而四時(shí)行焉,圣人不言鑒識(shí)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已彰。然則名之于物無(wú)施者也,言之于理無(wú)為者也。”可見(jiàn),鐘、傅所引“言不盡意”的觀點(diǎn),當(dāng)來(lái)自荀粲的影響。《鐘會(huì)傳》載:“中護(hù)軍蔣濟(jì)著論,謂‘觀其子,足以知人’。”據(jù)《蔣濟(jì)傳》載,濟(jì)任中護(hù)軍,約在太和二年(228年)冬以后,著論當(dāng)更在其后。其引“言不盡意”也在荀粲之后。《荀粲傳》載:荀粲“所交皆一時(shí)俊杰。至葬夕,赴者裁十余人,皆同時(shí)知名士也。”可見(jiàn),其在當(dāng)時(shí)的影響[6] (P. 112)。
因此,從歷史與邏輯相統(tǒng)一的視角來(lái)看,先有“言不盡意”論的重新提出,而后有“人物鑒識(shí)”問(wèn)題的提出和“名理之學(xué)”的產(chǎn)生。“名理之學(xué)”緣起于“人物識(shí)鑒”,以“人物偽似者多”為背景,而無(wú)論是儒家的“正名”還是法家的“刑名”或“形名”理論,不僅失去了原有的價(jià)值,而且面臨著嚴(yán)重的危機(jī)。而這種危機(jī)既是方法的危機(jī)、標(biāo)準(zhǔn)的危機(jī),更是價(jià)值和信仰的危機(jī)。這表明儒家傳統(tǒng)“名教”思想受到了嚴(yán)重的挑戰(zhàn)。因此,如何確定“名理”,即給某個(gè)人物以一定的名目時(shí),是根據(jù)外在的儀表舉止,還是根據(jù)內(nèi)在的精神氣質(zhì)?便成為人們必須面對(duì)的首要問(wèn)題[7]。而這個(gè)問(wèn)題的最終解決,固然,既有賴于圣人之意即經(jīng)典文本的意義追尋,又有賴于終極價(jià)值的形上追思和哲學(xué)建構(gòu),但并不是“言不盡意論”提出的直接原因。正是從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不是“言意之辨蓋起于人物鑒識(shí)”,而是“人物鑒識(shí)”有賴于“言意之辨”。而這恰恰也正是魏晉“言意之辨”的實(shí)質(zhì)、意義和價(jià)值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言盡意論”以“形名之學(xué)”的概念論、名實(shí)之間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為基礎(chǔ)(如歐陽(yáng)建),而主張“辨名析理”(如郭向等),其所“析”之“理”,不過(guò)是形下之“理”,而并非形上本體之“理”。其作為傳統(tǒng)的思想和方法,既是“言不盡意論”解構(gòu)的對(duì)象,又多發(fā)生在“言不盡意論”提出并成為主流思潮之后,所以,以“言盡意論”的提出“引起言不盡意之說(shuō),而歸宗于無(wú)名無(wú)形”為魏晉“言意之辨”的起源,顯然是不符合事實(shí)的。也就是說(shuō),魏晉“言意之辨”的興起,以“言不盡意論”的重新提出為濫觴,而有“言盡意論”的提出和詰難,不是“言意之辨蓋起于識(shí)鑒”,而是人物“識(shí)鑒”有賴于“言意之辨”。從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魏晉“言意之辨”發(fā)生、發(fā)展的過(guò)程,既是先秦“言意之辨”的主題思想、內(nèi)在精神和基本方法的價(jià)值回歸過(guò)程,也是兩漢經(jīng)學(xué)及其詮釋方法的解構(gòu)過(guò)程;既是天地之理和圣人之意——經(jīng)典文本的意義(言外之意、象外之意)——的追尋過(guò)程,也是玄學(xué)本體論哲學(xué)體系——終極價(jià)值的建構(gòu)過(guò)程。可以說(shuō),這既是玄學(xué)本體論哲學(xué)的顯著特征,也是玄學(xué)之為玄學(xué)的內(nèi)在根據(jù)和深層原因。
參考文獻(xiàn)
[1]湯用彤. 湯用彤全集(第5卷)[M]. 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2]湯用彤. 魏晉玄學(xué)論稿[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劉明武. “立象盡意”之“意”:元文化之源[J]. 人文雜志,2002,(6).
[4]皮錫瑞. 經(jīng)學(xué)歷史[M]. 北京:中華書(shū)局,1959.
[5]李霞. 易學(xué)詮釋原則與方法的演變[J]. 孔子研究,1999,(4).
第3篇
教師如何突破專業(yè)發(fā)展的限制?我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注意以下三點(diǎn):與其追逐名師的課堂,不如守住自己的班級(jí)。專業(yè)發(fā)展到一定的程度,尤其是到達(dá)發(fā)展“瓶頸”階段,需要的不再是盲目地追著名師的課堂跑。不可否認(rèn),有些名師早已離開(kāi)課堂,而一旦離開(kāi)課堂時(shí)間長(zhǎng)了,離開(kāi)學(xué)生的時(shí)間久了,說(shuō)出來(lái)的話、上出來(lái)的課,自然就不夠“接地氣”。有的名師的課像表演,“表演”不是課堂的常態(tài),不必學(xué)、不必追。與其像追星一樣追他們的課,不如看看他們課后在干什么、他們?nèi)粘5恼n是什么樣子。你必須找到他們的另一面,有些東西你才會(huì)恍然大悟。而最重要的是守住自己的“56號(hào)教室”,它比什么都重要,把它當(dāng)作一個(gè)世界來(lái)研究。當(dāng)你產(chǎn)生“給我一個(gè)班,我就心滿意足了”的感覺(jué)時(shí),你的專業(yè)發(fā)展想不突破也難。
與其看教育著作,不如多讀教育之外的經(jīng)典。讀教育著作,同樣該研讀經(jīng)典,須知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況且在名師出書(shū)熱潮中,難免魚(yú)龍混雜,其中絕大多數(shù)說(shuō)不上是“名著”,更遑論“經(jīng)典”。在有限的時(shí)間里,多讀經(jīng)典才是最經(jīng)濟(jì)的做法。然而,教育不是孤立的,僅讀教育經(jīng)典不足以真正懂得教育。教育是一口井,井外的天空很高遠(yuǎn)、很遼闊。文學(xué)、歷史、政治、經(jīng)濟(jì)、宗教等經(jīng)典為你打開(kāi)更廣闊的世界,哲學(xué)、社會(huì)學(xué)、人類學(xué)、心理學(xué)、生物學(xué)……讓你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理解別人。站在眾多的經(jīng)典面前,你會(huì)發(fā)現(xiàn),很多東西都是相通的。想突破專業(yè)發(fā)展的限制,你得先學(xué)會(huì)“懷疑”和“批判”,由此,走向“建設(shè)”之路。
與其寫(xiě)“科研論文”、做宏大的課題研究,不如腳踏實(shí)地做實(shí)證研究,哪怕做些原始資料的積累。一些骨干教師至今都認(rèn)為,寫(xiě)“科研論文”和做相當(dāng)級(jí)別的課題是專業(yè)發(fā)展的必由之路。其實(shí)未必,要看寫(xiě)什么論文、為何寫(xiě)論文,做什么課題、因何做課題。科研的本質(zhì)是求真。翻閱大量的“科研論文”,你會(huì)發(fā)現(xiàn)最缺乏的是“一份證據(jù)說(shuō)一分話”。不少論文,時(shí)尚的概念多、似是而非的結(jié)論多,少的是事實(shí),缺的是證據(jù)。如果真要突破專業(yè)發(fā)展的限制,就要不趕時(shí)髦,不趕潮流,踩著教育的節(jié)拍腳踏實(shí)地地走。不說(shuō)空話、套話,不寫(xiě)連自己都沒(méi)弄明白的文字,不要追求論文的“詩(shī)意”描述――教育是科學(xué),像醫(yī)生做病歷卡一樣,積累教育的原始資料比充滿“好詞好句”的論文要有價(jià)值、有意義得多。
其實(shí)所謂突破,無(wú)非是回到教育的本真,回到專業(yè)發(fā)展的正道上來(lái)。專業(yè)發(fā)展,要靠自己。
(本欄責(zé)編 再 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