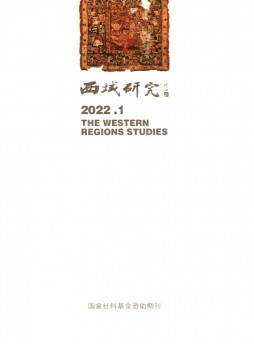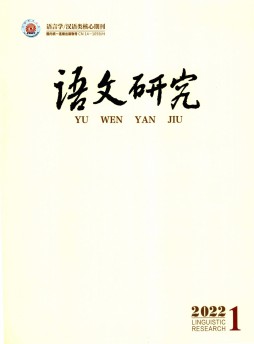西方美術(shù)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shù)篇優(yōu)質(zhì)西方美術(shù)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fā),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摘 要:本文通過對兒童藝術(shù)特點的剖析,揭示西方現(xiàn)代主義繪畫吸收和借鑒兒童藝術(shù)造型符號之后所形成的前所未有的率真、稚拙和清新的品質(zhì),并結(jié)合藝術(shù)家的具體作品分析進一步指出西方現(xiàn)代主義繪畫在本質(zhì)上有別于兒童稚拙藝術(shù),張揚著獨特的藝術(shù)個性,具有大巧若拙,拙中藏巧的藝術(shù)境界。
一、引 言
人們過去并未意識到兒童隨意而愉快的涂抹有什么特殊意義,更談不上對兒童藝術(shù)的發(fā)現(xiàn)及關(guān)注,然而,隨著人類藝術(shù)史上對兒童藝術(shù)的發(fā)現(xiàn)及現(xiàn)代藝術(shù)的產(chǎn)生,兒童藝術(shù)在當代藝術(shù)世界的位置正日益凸顯。現(xiàn)在,“兒童藝術(shù)”已是被普遍接受的概念,兒童藝術(shù)中那種形象的簡化、畫面的和諧、富有表現(xiàn)力的線條、大膽的純色平涂以及那種無意識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使得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家懷著新奇的目光從兒童藝術(shù)中汲取營養(yǎng)。
二、西方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大師對兒童藝術(shù)的認識與評價
兒童的作品究竟有何魅力?為什么會吸引全世界藝術(shù)家的目光?在兒童藝術(shù)中,兒童常常以其天真率直的心態(tài)每每使我們拍手稱快,是任何人為的方法都無法企及的。兒童藝術(shù)是無意識下創(chuàng)作的作品,是兒童心智和心緒的自然流露,往往呈現(xiàn)著藝術(shù)創(chuàng)作最初的也是最純粹的源泉。其構(gòu)圖造型稚拙有趣,似無法之法,有意想不到的生動。正如黑格爾所說:“兒童是最美好的,一切個別特殊性在他們身上好像都還沉睡在未展開的幼芽里,還沒有什么狹隘的東西在他們的胸中激動,在兒童還在變化的面貌上,還看不出承認繁復(fù)意圖所造成的煩惱,因而在兒童繪畫里表現(xiàn)出來的是他們對事物無意識的、天真率直的看法。133229.cOm”兒童藝術(shù)更具創(chuàng)造性和表現(xiàn)性,注重個人感受。兒童天性充滿熱情,能主動、自由地表現(xiàn)畫面,兒童看世界有他們自己的獨特眼光,他看起人來,只看到一個人的一個大頭,頭上的兩只眼睛,一個鼻子,一張嘴巴,什么耳朵、頭發(fā)、眉毛,他都沒有看見,所以他不畫一個人的身體,他看得不重要,只畫一條線來表示。這些入眼的觀察對象在兒童的心目中形象分外鮮明。兒童是畫其所想而非畫其所見,因此兒童畫出的作品往往想象豐富,用色大膽,富有生氣,有更多的靈性。西方現(xiàn)代派藝術(shù)中,反叛傳統(tǒng),追求單純和質(zhì)樸無華是其共同的目的和重要特征,因此,現(xiàn)代藝術(shù)家們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了兒童藝術(shù),而且給予兒童藝術(shù)以高度的評價,甚至對兒童的藝術(shù)狀態(tài)和兒童的藝術(shù)作品崇拜不已。現(xiàn)代藝術(shù)大師畢加索曾說過:“我曾經(jīng)能像拉斐爾那樣作畫,但我卻花了畢生的時間去學會像兒童那樣作畫。”這在當時是很有代表性的。其實這種對兒童藝術(shù)的新的認識和評價在野獸派那里已有所表現(xiàn)。康定斯基崇拜兒童藝術(shù)是因為他認為兒童藝術(shù)是對事物內(nèi)在本質(zhì)的直覺表現(xiàn),他說:“兒童除了描摹外觀的能力之外,還有力量使永久的內(nèi)在真理處在它最能有力地得以表現(xiàn)的形式中。……兒童有一種巨大的無意識力量,它在此表達自身,并且使兒童的作品達到與成人一樣高(甚至更高)的水平。”畫家馬蒂斯、杜飛、夏加爾,尤其是克利、米羅和杜布菲等,同樣感到了兒童藝術(shù)的魅力。西方藝術(shù)家所向往的那種無意識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信手涂抹”在兒童藝術(shù)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詮釋。
三、西方現(xiàn)代主義繪畫對兒童藝術(shù)的借鑒與模仿
從19世紀后半葉起,西方畫壇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眼花繚亂的西方現(xiàn)代畫派,既受到兒童繪畫在藝術(shù)形式上以及表現(xiàn)技巧方面的啟發(fā),更受到兒童對待繪畫的基本態(tài)度無意識的強烈沖擊。對兒童藝術(shù)的推崇與模仿直接反映在他們作品的形式中。克利就一直崇拜兒童的這種天真狀態(tài),并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模仿。克利在繪畫技巧上使用兒童那種環(huán)繞的、粗陋的輪廓線,反應(yīng)在作品《動物園》、《他喊叫,我們玩》和《女舞蹈家》中,這些畫中線條技法與兒童素描的線條技巧很接近,盡管它更細窄,更優(yōu)美。《高架橋的革命》畫面上簡單的甚至笨拙的高架橋,表現(xiàn)出了克利對兒童畫天真稚拙的形象以及符號化形象的興趣。在米羅的繪畫世界中同樣可以感受到這位大師對兒童藝術(shù)的推崇,在他1948年至1953年的許多繪畫作品中,人物沒有身體表現(xiàn),頭部直接安在以球形腳為末端的直腿上,整個臉像一個不規(guī)則的橢圓形或圓形,這種極端單純化的形象的變體,也就是兒童畫中的“蝌蚪人”樣式,如作品《在甲殼下部》、《黎明時瞪羚的哭叫》和《繪畫》以及早期最有名的作品《農(nóng)場》都已呈現(xiàn)出一種兒童般稚拙的風格傾向。后來由于戰(zhàn)爭,米羅的作品表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恐怖之感,但畫面依然保持他那種天真、優(yōu)美的風格。如系列《星座》及《女詩人》都是在戰(zhàn)爭的威脅之下創(chuàng)作出來的,但我們從中看不到任何血腥的痕跡。無怪乎有批評家說:“米羅的天才是一種返老還童的天才。”涂鴉和兒童藝術(shù)也是杜布菲的范例和靈感來源,他特別贊同用最簡單的正面和側(cè)面形象及兒童的輪廓線風格畫出大腦袋粗陋人物,也贊同兒童對記憶中傳達信息的細節(jié)的強調(diào),杜布菲甚至希望以更加粗蠻、直接和確定的方式拋棄“后天學到的手段”,去探討一條回到“藝術(shù)基本的、形成的時期,記錄下兒童式的天真與好奇狀態(tài)的道路”。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如《街上的男人》畫面中描繪的是巴黎的景色與生活,具有一種天真稚拙的趣味。此后,他很快擺脫了克利藝術(shù)中那種幻想、略顯天真的氣質(zhì),而轉(zhuǎn)向一種獨特的、奠定自己在藝術(shù)史上地位的繪畫創(chuàng)作方法,創(chuàng)作出一些涂鴉形態(tài)的作品,如在《人間的聯(lián)歡節(jié)上》,我們可以看到的一種以此法創(chuàng)作出來的令人厭惡和不安的歡樂氛圍。
西方現(xiàn)代派藝術(shù)中的荒誕和隨意性與兒童藝術(shù)中的荒誕和隨意是一致的。“荒誕藝術(shù)比起優(yōu)美、崇高的藝術(shù)更加深刻地表現(xiàn)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內(nèi)在生命力。”這是西方現(xiàn)代畫派對怪誕藝術(shù)的看法和推崇。現(xiàn)代派大師馬蒂斯、畢加索等人就從古代非洲的繪畫和雕塑中吸取怪異而又荒誕的特點,在我們的眼中極不符合常規(guī),但這與兒童美術(shù)中的無意識荒誕的想法極為相似。西方現(xiàn)代主義繪畫對兒童藝術(shù)的接受主要表現(xiàn)在欣賞他們的天然和單純,使得他們的作品具有稚拙的面貌,法國評論家在觀看他們的畫展時,曾稱這些顏色不符合“客觀實際”,藝術(shù)形象難以理解。雖說在現(xiàn)在看來有點言過其實,然而的確在馬蒂斯等人的作品中反映出畫家進一步轉(zhuǎn)向表現(xiàn)內(nèi)心情感,這也是近現(xiàn)代以來西方繪畫逐漸擺脫傳統(tǒng)上摹寫現(xiàn)實的主流畫法的新的一步,在野獸派繪畫中,馬蒂斯等畫家的一些人物畫有一個特點,人物的形象往往有彎曲的形態(tài)和封閉的輪廓線。如馬蒂斯的《浴者》和《海濱婦女》,這些作品使人想起兒童藝術(shù)的某些特點,人物的形象看起來“不準確”。上述這些對兒童藝術(shù)語言的模仿甚至直接挪用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現(xiàn)代藝術(shù)家們從兒童那里重新獲得天真、純樸和清新的內(nèi)在品質(zhì)。
四、現(xiàn)代主義繪畫大巧若拙
現(xiàn)代主義繪畫在許多方面更借鑒兒童藝術(shù),但他們的目的并非簡單地重創(chuàng)兒童繪畫,在技巧、表現(xiàn)形式上與兒童繪畫有很大差別。兒童繪畫是在生命之初對世界的探索嘗試,表達的是整個生命尚未展開的天性。而大師的繪畫則是在生命成熟階段對探索世界的提煉總結(jié),表達出整個生命發(fā)展過程凝結(jié)出來的人格特征和藝術(shù)個性。所以,兒童畫一張張來看,大不相同,而大面積看起來,其面貌給人的感覺大同小異。大師繪畫則不同,都具有獨一無二性。克利、米羅和杜布菲等現(xiàn)代畫家在對兒童藝術(shù)的借鑒中充分展示了各自的藝術(shù)個性,他們使用兒童的符號和技法也并非偶然,而是他們比其他藝術(shù)家更需要這種敏銳的感覺力,帶著激情去感受兒童的繪畫世界。他們的繪畫有著精致的層次和精湛的技巧,雖然繪畫的最終效果有著明顯的隨意性,但與兒童天真的藝術(shù)并未完全融合,保持著各自的獨立性,又相得益彰。兒童的繪畫作品是“原始”形態(tài)的、天真純樸的,而又往往以“稚拙”的樣式表現(xiàn)出來。這在兒童是很可貴的,也是許多中外畫家所追求的藝術(shù)境界。那么藝術(shù)家追求的天真純樸和稚拙與兒童繪畫所表現(xiàn)出的天真純樸和稚拙是否如出一轍呢?這對于我們更深一步了解兒童藝術(shù)是至關(guān)重要的。審美創(chuàng)造一般都是由拙到巧、再由巧返拙的階段。開始之拙,是生疏幼稚的真拙,隨著審美創(chuàng)造技巧的提高,進入精巧工巧階段,有了豐富的經(jīng)驗、功夫、素養(yǎng),才能落盡繁華歸于樸淡,進入大巧若拙的境界。沒有深厚的功底,片面為拙而拙,只會粗陋低俗。戴復(fù)古說:“樸拙唯宜怕近村。”(《論詩十絕》)即使是巧后之拙,如果刻意追求拙的外在形式,則是一種造作,失去其真正的天然本質(zhì)。拙樸絕非粗率平庸之輩所能達到的,它是審美創(chuàng)造高度成熟的標志。追求兒童趣味的藝術(shù)家在某些方面與兒童繪畫較為相似,例如:以線為主,平涂色彩,不講焦點透視及夸張變形手法等等。但兒童藝術(shù)中的那種天真稚拙的情趣被藝術(shù)家們加以發(fā)揮、拓展,成為嶄新的藝術(shù)形式。雖然他們畫中的“拙”與兒童繪畫中的“拙”有著形式上的相似,但卻又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他們是老子所說的“大巧若拙”之“拙”。寫意大師崔子范也曾說:“一個沒有受過專業(yè)訓練的孩子只憑熱情作畫。在他長大之后,也應(yīng)該注意使自己回到童年的心態(tài),去重新發(fā)掘自己兒時的天性——自由地而不是造作地在畫中表現(xiàn)自己的感情。當一個成熟的畫家運用這種方式作畫時,當他將藝術(shù)大師的精湛技巧與孩子般的天真爛漫融合在一起時,會感到極大的快慰。”雖然西方的克利、米羅和杜布菲等畫家的作品源于兒童繪畫的造型符號,但他們靠熟練精深的技巧來完成。大體上都經(jīng)歷了由開始的不成熟,到技法日趨精深,進而追求“返璞歸真”的過程。雖然也有追求兒童“拙味”的畫家未經(jīng)過專門的訓練,但他們也難免經(jīng)受藝術(shù)傳統(tǒng)的熏陶,前輩及同代畫家的影響與個人技巧的錘煉。克利雖曾說:“無需什么技巧”,但他畢竟經(jīng)過了傳統(tǒng)藝術(shù)熏陶,其藝術(shù)風格必有傳統(tǒng)技巧的痕跡。可見兒童的稚拙是幼稚的拙,而畫家的稚拙是“拙中藏巧”之拙。“拙樸最難,拙近天真,樸近自然,能拙樸則渾厚不流為滯膩。”拙樸之拙,是大巧,不露痕跡,使人不覺其巧。它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濃”(《東坡題跋》),在平實樸素粗散的形式中,蘊含著深厚的審美素養(yǎng)和豐富的情感意味。沒有一定技巧的錘煉,一味片面追求兒童“拙味”,只會流于粗俗淺薄,達不到自然渾化的拙樸之境。
五、結(jié) 語
總之,現(xiàn)代藝術(shù)家們從兒童藝術(shù)中獲取到了造型符號的靈感,同時也通過自己的作品和言論促成了人們對兒童藝術(shù)的進一步關(guān)注、承認和了解。在現(xiàn)代藝術(shù)中,傳統(tǒng)的審美標準首先被打破,幾乎沒有什么尺度可以將兒童藝術(shù)與大師的作品相區(qū)別。當然,西方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家的作品與兒童的繪畫作品之間的相仿程度,也不能真正完全劃上等號,這些現(xiàn)代藝術(shù)大師的繪畫畢竟是落盡繁華歸于樸淡,大巧若拙,拙中藏巧。
參考文獻:
[1] 羅伯特·戈德沃特.現(xiàn)代藝術(shù)中的原始主義[m].殷泓譯.南京:江蘇美術(shù)出版社1993:54.
[2] 阿恩海姆.藝術(shù)與視知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3] 崔慶忠.現(xiàn)代美術(shù)史話[m].北京: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1.
第2篇
關(guān) 鍵 詞:現(xiàn)代繪畫 交流 融合 影響
西方近代美術(shù)史的演變,曾被人喻為一個傳奇性的故事。由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人們千變?nèi)f化的價值觀念,打開了許多未曾探索過的道路。一直到現(xiàn)在,“現(xiàn)代美術(shù)”仍是個令人迷惑的名詞,一些被公認為藝壇巨人的畫家,如塞尚、馬蒂斯、畢加索雖已成為藝術(shù)史上的傳奇人物,卻仍然經(jīng)常被一般人所忽略,畢加索的立體派或荒唐或有趣,馬蒂斯的野獸主義或美觀或滑稽。但是這些“巨人”是如何創(chuàng)造出如此與眾不同的藝術(shù)流派的呢?他們的經(jīng)歷既辛酸又坎坷。在現(xiàn)代歐洲藝壇中,野獸派代表人物馬蒂斯,西班牙超現(xiàn)實主義畫家、抽象派繪畫的先驅(qū)者米羅,兼具立體主義、超現(xiàn)實主義、表現(xiàn)主義等多種風格的俄國斯畫家夏卡爾,均為極負盛名的大師,被推崇為藝壇一代宗師。
1910年,馬蒂斯在慕尼黑觀賞了轟動一時的近東藝展,那次藝展對于他日后的繪畫方式,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力。近東的藝術(shù)富于艷麗逼人的色彩,而且也偏重于平面式的構(gòu)圖,用強烈而鄉(xiāng)間的純色彩、阿拉伯式的藤蔓花紋和各種只有東方味道的平面圖案。在他繪畫生涯的后期,馬蒂斯開始用彩色的紙,剪成彩色圖案,再用蠟筆和塑膠水彩來掩飾晚年以及疾病帶給他的不便。WWw.133229.CoM馬蒂斯的藝術(shù)之所以不朽,因為他包容了大自然,能夠讓自己同大自然合二為一,與大自然的韻律起步而行。這一點同我國老子、莊子的順其自然頗為近似。“莊周夢蝴蝶,蝴蝶夢莊周,萬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萬體更變易”便是馬蒂斯所強調(diào)的重點之一,人在不同的時候看同樣的一件東西,觀察的角度不可能完全一樣。西方美術(shù)自14、15世紀文藝復(fù)興以來,一向強調(diào)“獨一立足點”論,這是與東方美術(shù)完全不同的地方。東方美術(shù)幾乎不使用一個固定的立足點,一幅畫總是由許多不同的立足點來構(gòu)成,馬蒂斯所擁有的,就是我們東方美術(shù)的這種“多重立足點”的觀念。因此他的畫顯得格外生動活潑,一點也不死板。馬蒂斯的空間利用恰巧符合我們“陰陽相間”的理論。馬蒂斯利用空間促使了畫中物體間氣韻的順暢,舉世聞名的現(xiàn)代美術(shù)評論家羅杰·弗萊在1912年評論馬蒂斯是所有西洋畫家中最了解中國美術(shù)精神的一位,這種啟發(fā)生命的韻律感,以及相對論的道理,確實是中國美術(shù)所強調(diào)的重點。他還認為:“第十、十一、十二世紀的藝術(shù),亦即羅馬式藝術(shù),包含很多東方藝術(shù)的成分,這些成分在當時還伴隨其他貨品,由東方輸入伊斯坦布爾、威尼斯,這些成分貢獻很多,它們經(jīng)過轉(zhuǎn)變,有了新的生命,而顯豐饒,它們開發(fā)新道路,也形成新環(huán)節(jié)。1920年的《宮女》,畫中的東方色彩(尤其是對波斯纖細畫的喜愛)以及作者筆下簡單的僧侶式人體、繁縟的背景同樣是扣人心弦的組合。他對線條的抽象、和諧、節(jié)奏的追求,強烈得常使人體的自然表象剝落盡至。”這樣的說法是正確的,無論如何,這時期的畫意念非常豐富,人體的簡化與靜物畫裝飾細節(jié)的增濃并進。原因之一,是他長久以來對東方藝術(shù)的喜愛,這份喜愛在1910年9月他赴慕尼黑參觀回教藝術(shù)展時達到巔峰,后來他曾說:“我的靈感是來自東方。波斯纖細畫啟示我感官的一切可能,緊密的細節(jié)暗示出更大的空間,并幫我超越披露個人感情的繪畫表現(xiàn)。”馬蒂斯非常喜歡阿拉伯的蔓藤花,是緣于回教藝術(shù)的直接影響(日本版畫也有)。“我曾用彩色的紙做了一對小鸚鵡,我在作品中找到自己,中國人說要與樹齊長,我認為再也沒有比這句話更認真的了。”馬蒂斯晚年熱衷于剪紙藝術(shù)時說了這段獨白,他把東方的剪紙視為完全美的化身,從剪紙畫中得到過去從未有過的平衡境界。不取西方古典油畫的三維立體塑造,基本上是在二維空間的平面構(gòu)成中展示自己的彩色夢幻。但是由于彩色板塊里加進了黑白板塊的分割、隔離以及物象的排映、濃濃的交織,畫面呈現(xiàn)出多重的空間層次,不僅生成平面的張力,而且生成縱深的張力,從而產(chǎn)生一種疊幻的視覺牽引力,使畫面欣賞起來如層層剝筍,十分耐品。他的靈感常常來自東方藝術(shù),用純色平涂,色彩鮮艷,但并不“野獸”般刺激,他夢想的是一種平衡、純潔、寧靜,不含有使人不安或令人沮喪的題材的藝術(shù),它像一種鎮(zhèn)定劑,或者像一把舒適的安樂椅。
在西方現(xiàn)代畫家中,保羅克利對東方人來說是最親近的。他的藝術(shù)觀念和東方神秘主義相通,即把創(chuàng)作活動視為不可思議的體驗,而這一體驗過程乃是內(nèi)部幻覺與外界真實的統(tǒng)一,其哲學根源在人和自然之間本質(zhì)上的同一性。
自1916年至1917年,克利專攻中國文學,接觸到中國書法和中國畫,從中汲取了文字可以造型的思想,并以獨特的方式進行了實驗。這一研究結(jié)果就是一系列的文字畫。而且以后還以單個的較大r字母出現(xiàn)在繪畫中,克利的繪畫藝術(shù)中,體現(xiàn)了中國繪畫的影響,在《隱士的住所》中的那所簡陋的小屋,是中國山水畫的面貌,不過,在這幅作品中,房屋的側(cè)面卻豎有十字架,它告訴人們這位隱士不是中國人。克利在藝術(shù)上與中國最重要的關(guān)系,與其說是主題還不如說主要表現(xiàn)在繪畫內(nèi)容上,尤其在中國文學中常見的大自然與孤獨者之間的對話,對克利產(chǎn)生了強烈的共鳴;與其說是受到中國的影響,還不如說是對中國的再認識。如他畫的《中國風俗畫i》《中國風俗畫工ii》和《曾經(jīng)在灰蒙蒙的夜色下徘徊》一樣,本來是完整的一幅,后來被裁為各不相同的兩幅作品,旨在表現(xiàn)中國油畫的風格。他在創(chuàng)作《中國風俗畫》前還有一個作品,編號是《中國陶器》。由此看來,在一段時間內(nèi),克利對中國產(chǎn)生了很深的感情。《大路與小徑》,都融會在這大大小小完全抽象的格狀作品中,垂直線和畫面,象征著廣闊的埃及原野,它們以多變的寬度,向著頂端的天藍色帶——尼羅河延伸;在斑斕的色彩映照下,廣闊的田野與顫動的空氣融為一體,大地流水、太陽、春光充滿著永恒的詩一般的境界,整個畫面形式與韻律結(jié)構(gòu)氣勢恢宏,這(轉(zhuǎn)第105頁)(接第108頁)與中國講究的人與自然相融合至高境界的理念是相符的。
克利在晚年的繪畫中使用很粗的線條,有些像中國的書法,“筆跡最關(guān)鍵的是表現(xiàn)而不是工整,請考慮一下中國人的做法。我們在反復(fù)練習的過程中,才能使筆跡變得更為細膩、更直觀、更神韻。”這是他的體會,克利依靠自己高度集中的精神,達到了與東方藝術(shù)家并駕齊驅(qū)的境界。像《鼓手》這幅畫,乍看幾乎和中國現(xiàn)代書法差不多:像“寫字”一樣的單純的黑色線條,在簡潔的形態(tài)中隱藏著深切的感動。此時,克利的手足已不能自由活動,于是他用最少的視覺語言記下了最后最多最明確的話語,熱愛音樂的克利,回憶起少年時代作為一名鼓手參加伯爾尼市管弦樂團的演奏,便創(chuàng)作了這幅畫。大大的眼睛,強有力的胳膊,以及畫面的深紅色,表示他自己對人生執(zhí)著的追求,同時讓人感到在內(nèi)部隱藏著冷酷的命運。常常“先行而后思”,不斷在實踐中思考總結(jié)自己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參照他的繪畫,可以看出他“緊緊抓住‘綜合鏈條’,通過‘博大精深’,走向‘天人神會’”的創(chuàng)作思路。“天人神會”是克利追求的最高境界。畫天宇、畫日月,亦可見其所求。“博大精深”是克利經(jīng)歷的意象升華。他認為繪畫語言的“非陳述性”表現(xiàn)為直觀性、可感性、符號性、有機性、意象性;而這些特性在中國畫里則體現(xiàn)為既非“具象”也非“抽象”而是“主客觀高度濃縮統(tǒng)一的形象”,即超乎“具象”與“抽象”的“意象”和“意境”。
筆者聯(lián)想到與之視覺語匯相近的中西兩種藝術(shù):一是漢代畫像石的拓片。漢代畫像磚、畫像石的拓片就是一種影像,是不見骨線卻很有力度、很有動感的一種影像。東方思維方式不像西方那樣主客對立、內(nèi)外分明,但由于修養(yǎng)、閱歷和個性之異亦各有所側(cè)重。
第3篇
《圣經(jīng)·馬太福音》曾說:“在黑暗中開黎明”。這一語道破了光在這個世界中的位置,因為它是一切萬物得以顯現(xiàn),并且被賦予生命的神奇物質(zhì)。同樣,在研究或欣賞西方繪畫,尤其是傳統(tǒng)繪畫時,我們更不能忽視光的神奇力量。光在西方繪畫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有了光,便有了體積,有了形狀,有了色彩。因此,西方繪畫對光的運用集中體現(xiàn)在真實性藝術(shù)之中,要粗略給個范圍的話。這大概是從古希臘開始,一直延續(xù)印象主義,這以后的藝術(shù)雖然仍有不少具象繪畫,但就整個藝術(shù)史來看,它已經(jīng)不再是主流,所以從現(xiàn)代主義開始的西方繪畫不在本文討論的范圍之內(nèi)。
在西方繪畫史的長河中,對光的運用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古希臘羅馬到文藝復(fù)興。在這個時期,對光的運用是為了通過制造幻覺達到描述的作用。藝術(shù)從古埃及到古希臘的轉(zhuǎn)變。正是古希臘人認識到光的重要,從而認識到明暗。認識到色彩,達到對真實的表現(xiàn)。古羅馬的繪畫在龐貝和赫庫蘭·尼姆的死者肖像中可略知一二,在這些繪畫中,我們看不到太多的“光”,它們是通過把光消解在陰影和明暗中來摹擬物象,是對光被動地接受,光化為了形體。在中世紀,古希臘、羅馬的繪畫傳統(tǒng)在拜占庭帝國中得到延續(xù),以至以后的印象派畫家雷諾阿在威尼斯圣·馬可大教堂看到拜占庭的畫時發(fā)出感嘆,認為光和色的奧秘早已被中世紀的畫家所識破。WWw.133229.CoM
第二階段從文藝復(fù)興到十八世紀,在這個階段對光的運用可用一個詞來概括:設(shè)計。對光的運用強調(diào)一種人工性的設(shè)計,這基于對光的獨立表現(xiàn)力的認識,光并不只是為了造成塑造形體的明暗。而且是為了氣氛、環(huán)境的渲染或體現(xiàn)畫家的某種思想。馬薩喬是自喬托之后第一個在才能上與之不相上下的畫家,從他的處女作《寶座上的圣母子和二天使》中可以看出,他的革新精神已初露鋒芒,他的人物較之喬托的畫更加真實有力,畫中的背景具有一種親切的真實感。同時還證明他是通過光第一個廣泛運用明暗對比手法的人;第一個掌握透視法的人。馬薩喬的業(yè)績給同時代的和后來的畫家們以極大的影響,他們?yōu)榱藢W習馬薩喬的技法,研究他完美的寫實技巧、空間的表現(xiàn)、人物的安排和優(yōu)美的造型,并最終形成了佛羅倫薩畫派的寫實主義潮流。文藝復(fù)興的盛期美術(shù)一方面總結(jié)了十五世紀美術(shù)的經(jīng)驗。把透視、解剖、明暗等寫實的手法發(fā)展到了盡善盡美的地步:另一方面有汲取了古典藝術(shù)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形成了莊重典雅的藝術(shù)面貌。同時,大師們進一步把藝術(shù)與實驗科學、創(chuàng)作實踐與理論研究結(jié)合起來,進一步推進了寫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
在這一階段對光的設(shè)計歸納起來有兩種:一種是燭光效果,以尼德蘭的托特·辛特·楊斯的《基督誕生》及法國的喬治·拉圖爾的“夜間畫”為代表:另一種影響最大的是明暗對比效果,從達·芬奇的“漸隱法”開始(作品《蒙娜麗莎》便可看出其成就)。到卡拉瓦喬的“酒窖光線法”(預(yù)示著歐洲十七世紀現(xiàn)實主義繪畫發(fā)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再到倫勃郎的“明暗法”。在這個設(shè)計光線的階段,著重的是一種亮與暗的對比,在這種對比中既表現(xiàn)出形象,也傳達出一種形而上的思想。可見這時光的運用已成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