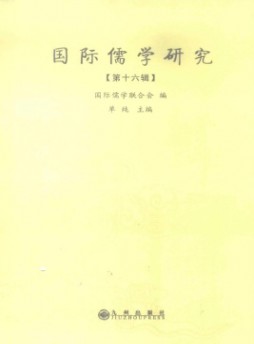儒家文化哲學(xué)研究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shù)篇優(yōu)質(zhì)儒家文化哲學(xué)研究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fā),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核心觀點(diǎn): 新儒家是指堅信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中國仍有價值,認(rèn)為中國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價值,謀求中國文化和社會現(xiàn)代化的一個學(xué)術(shù)思想流派。
新動向:儒家文化在民間社會和知識界一直處在復(fù)興之中,并呈加速趨勢。復(fù)興的趨勢,由早期以兒童為對象,以儒家經(jīng)典為主的傳統(tǒng)文化經(jīng)典誦讀活動,演變?yōu)橐猿赡耆藶橹鞯淖x經(jīng)修行活動。
在新儒家群體看來,儒家文化的當(dāng)代身份問題,可以轉(zhuǎn)換為當(dāng)代儒家文化團(tuán)體和儒者個體的組織化問題,以及儒家文化復(fù)興的現(xiàn)實(shí)路徑問題。2012年新儒家發(fā)展的年度特征,主要表現(xiàn)為上述兩方面勉力探索和形成共識。
儒家的組織化
2012年10月29日,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在北京薊門橋主辦“儒生重現(xiàn)之文化、歷史意義暨‘儒生文叢’出版座談會”。“儒生文叢”第一輯共有三冊,書名分別為:《儒教重建——主張與回應(yīng)》,《儒學(xué)復(fù)興——繼絕與再生》,《儒家回歸——建言與聲辯》,這三冊書可以視作最近十余年儒家文化復(fù)興的理論成果匯編,故而書籍的出版引起學(xué)術(shù)界和思想界高度關(guān)注。與此同時引起關(guān)注的還有這套文叢對“儒生”一詞的使用。區(qū)別于儒家文化的普通研究者,“儒生”更強(qiáng)調(diào)個體對儒家的認(rèn)同、儒家復(fù)興的擔(dān)當(dāng)和儒家思想的踐行。儒生應(yīng)具備極高的典范人格和良好的學(xué)術(shù)品格,能夠影響和造就一批以成就君子而自勵、具有高尚人格品行的儒生,帶動儒生群體的形成,傳播儒家學(xué)說。這是實(shí)現(xiàn)儒家文化快速發(fā)展的正確路徑。
有了儒生,下一步還要有儒生的團(tuán)體組織,以組織的形式將全國自發(fā)的、松散的儒生個人和儒家社團(tuán)聯(lián)合起來,以便以一個統(tǒng)一的身份代表儒家,以及加強(qiáng)儒家團(tuán)體和個人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鑒和相互幫助。2012年11月25日,一個由學(xué)生社團(tuán)演變?yōu)樯鐣F(tuán)體的“儒社”正式成立,該社的宗旨是“崇文尚武,忠孝節(jié)義”。成立當(dāng)天,儒社和在京多家儒家團(tuán)體共同舉辦祭孔典禮,并舉行了“儒士與當(dāng)代社會”學(xué)術(shù)研討會。令人驚奇的是,會上還有兩名地方大區(qū)的負(fù)責(zé)人,分別匯報了各自地方儒社開展工作的情況。2012年末至2013年初,新儒家部分代表還將就全國性儒家社團(tuán)的形成和組織問題進(jìn)一步商議。儒家組織化的目標(biāo)是形成一個全國性的儒家社團(tuán),征得政府和社會的承認(rèn),代表儒家的當(dāng)代身份和維護(hù)儒家的文化利益。
儒家復(fù)興的路徑
2012年,儒家群體在儒家復(fù)興的具體路徑方面有了更多討論,也達(dá)成一些重要共識。儒家在當(dāng)代復(fù)興的具體路徑,仍然是沿著清末康有為開出的三條道路繼續(xù)前進(jìn)。這三條道路分別是儒學(xué)、儒術(shù)和儒教。
所謂儒學(xué)就是把儒家文化首先當(dāng)成是一種學(xué)說,以發(fā)展儒家學(xué)說的方式來發(fā)展儒家文化。康有為是第一個借用西方哲學(xué)的方式來撰寫儒家著作的人,也可以稱得上是中國第一位“哲學(xué)家”,在他以后的很長時間內(nèi)儒學(xué)主要地就保存在“中國哲學(xué)”這個學(xué)科里。當(dāng)前儒學(xué)發(fā)展的一個新特點(diǎn),是國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經(jīng)學(xué)的復(fù)活,以及社會科學(xué)普遍出現(xiàn)重視和回歸儒家文化的做法。
儒術(shù)則是發(fā)揮儒家文化的外王功能,以儒家倡導(dǎo)的仁愛為出發(fā)點(diǎn),重構(gòu)社會秩序,追求理想之治。中國人對政治本質(zhì)的認(rèn)識和政治興替規(guī)律的把握,一直有其深刻和獨(dú)到之處,當(dāng)代中國政治中的一些重要語匯,諸如小康、民本、和諧、惠民、民心向背等都出自儒家,甚至于論證執(zhí)政的合法性問題,也還是要回到傳統(tǒng)儒家的政治邏輯。當(dāng)前儒家社會科學(xué)恰恰表現(xiàn)出一種很是明智的做法,面對中國現(xiàn)實(shí)問題時,將西方思想和儒家思想相結(jié)合。這種結(jié)合并不是生硬地比附,而是回到儒家傳統(tǒng)中找出當(dāng)代思想的本原和根基,并為儒家諸如仁政、民本政治、和諧政治、大同社會等政治原則和政治追求,尋求適應(yīng)的現(xiàn)代形式。2012年比較具有影響的一個會議是10月27日在清華大學(xué)召開的“全國政治儒學(xué)與現(xiàn)代世界研討會”,會議的一個主要議題是討論儒家“賢能政治”的當(dāng)代意義。《文化縱橫》在3月份發(fā)表的有關(guān)“人民儒學(xué)”的三篇文章,代表著政治儒學(xué)堅持和發(fā)展儒家學(xué)說人民性的最新動態(tài),探求以民主、法治去承接儒家政治思想核心中的人民性與革命性。一些儒家學(xué)者重寫中國秩序史和重新討論儒家人權(quán)學(xué)說,也都為我們重新觀察儒家政治思想和中國古代政治史提供了新的視角。
儒術(shù)是儒家學(xué)說落實(shí)于社會的方式,儒教則是儒學(xué)落實(shí)于人心的方式。儒教關(guān)注的是以儒家文化來幫助解決信仰問題。一些儒家學(xué)者將儒教作為儒家文化在當(dāng)代可能存在的一個身份,為儒學(xué)的靈魂找到一個聯(lián)系大眾的身體,而另一些儒家學(xué)者認(rèn)為儒教形態(tài)有可能使儒家文化與佛教、道教一樣,成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而喪失了曾經(jīng)擁有的無所不在的“國教”身份,同時也為進(jìn)入教育和政治體制內(nèi)部帶來障礙。此外,一些學(xué)者主張儒教應(yīng)當(dāng)徹底告別政治,走純粹民間化宗教的道路,只關(guān)注信仰,不牽涉政治;一些學(xué)者則主張恢復(fù)儒教的國教地位,走官方路線。這其中的爭論很多,一時也達(dá)不成一致意見,惟一達(dá)成共識的是各種探索,各自實(shí)踐。2012年最為關(guān)注的事件則是儒家學(xué)者群體關(guān)于河南周口平墳事件的兩度連署請愿和撰寫相關(guān)文章。
如何看待正在興起中的新儒家思潮
既不必把新儒家看作是當(dāng)代思想中的異端,也不必把新儒家看作是當(dāng)代社會中的另類。儒家在歷史上其實(shí)是一再衰落,可又一再興起。個中原因無非在于,人們始終要回歸儒家以人民為“天”的政治信條,以仁愛建立家庭秩序和社會秩序的常道,以上下各自端正和相互校正、相互匡正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設(shè)計。
儒家的老店開了兩千多年,儒生為每一代統(tǒng)治者講述“政者,正也”和“民貴君輕”的道理,儒家迎來又送走了一個又一個王朝。任何一個自以為是開天辟地的朝代,最后都得老實(shí)承認(rèn)圣人從堯舜以來幾千年悠久歷史中總結(jié)出來的道理,果真是顛撲不破。新儒家也好,儒生也罷,都不是什么特殊的一類,只不過是在我們這個時代較早認(rèn)識到這一點(diǎn)的社會成員而已。
當(dāng)我們整個社會通過弘揚(yáng)儒家文化精華而把弘揚(yáng)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真正落在實(shí)處的時候,當(dāng)我們每個人都繼承中華民族先民“祖述堯舜”、“天下為公”的政治追求,走在邁向“大同”之治的中國夢的路上時,我們每個人都是新儒家。
第2篇
關(guān)鍵詞: 儒家文化 異同
自思想進(jìn)入中國以來,它在傳播的過程上就不可避免的與中國的本土文化――儒家文化發(fā)生融合,碰撞。兩者雖然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經(jīng)濟(jì)基礎(chǔ)、政治制度,但是如果將兩者相互比較,還是會發(fā)現(xiàn)他們的一些共同之處。對這個問題的分析,也有著深遠(yuǎn)的現(xiàn)實(shí)意義。
一、從本質(zhì)上探究與中國儒家文化的差異
由于產(chǎn)生的背景各不相同,兩種文化所服務(wù)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與政治制度是各不相同的,其所代表的也是完全不同的階級的利益,所擁有的社會文化功能也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思想體系。所以在探究二者關(guān)系之前,我們有必要將它們之間的界限劃清。
(一)文化背景差異
及其思想來源都是在歐洲資本主義文化背景孕育的。而其存在的意義便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之下超越歐洲的資本主義文化。
而儒學(xué)文化的產(chǎn)生背景則與相差甚遠(yuǎn)。由孔孟起始的原始儒學(xué)其誕生背景主要源于農(nóng)耕文明和血緣家族文化。由農(nóng)耕文明所催生的以自然道理為基礎(chǔ)的中國式的形而上學(xué),由血緣家族文化中誕生了尊卑有序,貴賤有別的倫理觀念。而在宋代誕生的新儒學(xué),主要以皇帝為中心的政治儒學(xué),其實(shí)現(xiàn)的基礎(chǔ)便是對皇權(quán)中心主義與封建官僚制度的擁護(hù)。
(二)時代精神差異
時代精神對特定時代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力。它是時代價值取向的代表者,以前驅(qū)性和進(jìn)取性為特質(zhì),具有正面價值。而哲學(xué)通常都是時代精神通的表現(xiàn)載體。哲學(xué)家,是特定時代特定背景下產(chǎn)生的產(chǎn)物,是匯聚了那個特定時代下最精致、最隱蔽、最珍貴的精髓哲學(xué)思想的產(chǎn)物。因此,馬克思說,哲學(xué)是文明活著的靈魂。
哲學(xué)是在歐洲資本主義制度趨于成熟的時代下誕生的。在這個時代下,資本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chǎn)和私人占有生產(chǎn)資料的生產(chǎn)形式之間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社會矛盾,無法避免的帶來經(jīng)濟(jì)危機(jī)與社會危機(jī),而此時擁有著代表社會新的生產(chǎn)力特征的無產(chǎn)階級,以其擁有的大而先進(jìn)的生產(chǎn)力、政治力,在歷史的舞臺上登場。而哲學(xué)便是無產(chǎn)階級這種強(qiáng)大力量的代表。
原始儒學(xué)則是在一個王室衰微,諸侯爭霸,禮樂崩壞的時代,當(dāng)時的時代精神反映了亂中求治的時代需求,于是原始儒學(xué)便在那個條件下應(yīng)運(yùn)而生。孔子以“復(fù)周禮,緬三代”的為思想為核心,展示了克己、復(fù)禮的大義。而亂世思治的時代同時也為他提供了一個展示由他構(gòu)想的理想境界中的世界的機(jī)會。從而使儒家思想在那個時代成為了價值中心,從民族的角度來講,激發(fā)民族凝聚力是價值中心的重要使命。
儒學(xué)文化與哲學(xué)各自所具有的時代精神是各不相同的,兩者中間有著兩千年的歷史跨度,并不是同時空的精神產(chǎn)品,它們各自在歷史中的勢位高低,自然一目了然。
(三)代表觀念和階級意識的差異
作為代表先進(jìn)的近代物質(zhì)生產(chǎn)力的,它反映了在資本主義大背景下相互對立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間的相互斗爭和無產(chǎn)階級根本利益。由于在意識形態(tài)性上與資產(chǎn)階級政權(quán)在根本上是對立的,是具有革命性的哲學(xué)。所以,他不可能成為現(xiàn)存國家的擁護(hù)者和衛(wèi)道士,它是它們的摧毀者和掘墓人。
與相比,儒學(xué)思想在意識形態(tài)上就不備有這種革命性。在其創(chuàng)立之初,雖然也有著代表非權(quán)貴群體利益的思想,但是其思想終究也只是來自于沒落貴族階級,依然具備著階級意志。自漢唐以來,儒學(xué)思想便成為了中國封建社會用以維護(hù)封建皇權(quán)利益的官方正統(tǒng)哲學(xué)。
與儒家文化從其階級性和革命性的立場上來講,是根本對立的,是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
二、異中有同的與中國儒家文化
與儒家文化雖然在根本上存在著巨大差異,但是二者之間也擁有著共同之處。如果對這一點(diǎn)不能做出正確認(rèn)識,就可能對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不全面的認(rèn)識,同時也可能無法理解中國化過程中,其在本質(zhì)中與中國儒家文化所發(fā)生的相容與相通。這兩種在時代性與階級性上有著本質(zhì)性區(qū)別的思想體系,在學(xué)說上卻可以找到一些相似、相通、相容之處。
與儒家文化在世界觀上都具有無神論的特點(diǎn),其思想有著反對神學(xué)、宗教的特點(diǎn)
由于曾經(jīng)受到“左”思潮影響,曾經(jīng)不加分析的將儒學(xué)完全歸類為唯心思想、形而上學(xué),其實(shí)儒家學(xué)說是不講“怪、力、亂、神”,并且一直對神學(xué)保持著懷疑。而哲學(xué)則是科學(xué)的無神論,其以對神學(xué)理論的徹底否定在歐洲思想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雖然在對社會進(jìn)行改造的理論上與儒學(xué)思想有著極大的區(qū)別,但是它們都是反對通過非人類的力量來改造社會的。兩者都重視現(xiàn)實(shí)社會與現(xiàn)世人生的思想。以此來看,在無神論的觀點(diǎn)上兩者是有著相通之處的。
在道德觀上,中國儒學(xué)文化和也有著相同之處,兩者對人擁有的自然屬性,及與此相應(yīng)的表現(xiàn)形式,所具備的合理性表示接受,但是同時又認(rèn)為人的自然屬性應(yīng)該受到社會屬性的約束,并對其進(jìn)行規(guī)范,才能達(dá)到完善的人性。在儒家思想中,也有著“食色性也”和“為惡去善”這樣的體現(xiàn)。雖然馬克思對維護(hù)個人的自由和權(quán)力十分重視,但是他也認(rèn)為個人解放是必須要在全人類解放的大前提下才能夠達(dá)成的。這與儒家思想中的“克己復(fù)禮”的價值觀是相通的。
三、結(jié)語
在中國儒家文化與中,有著諸多的相通之處,但是這種相通卻并不意味著完全一致,而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而在中國能夠順利發(fā)展的基礎(chǔ)便是與儒家文化在碰撞與摩擦后的相容、相通。
參考文獻(xiàn):
[1]牛蘇林.宗教觀研究應(yīng)關(guān)注的幾個基本理論問題[J].中州學(xué)刊,2015,(12).
[2]王晶,王雅舒.探析中國化的三種角度[J].文藝生活?文藝?yán)碚摚?010,(08).
第3篇
關(guān)鍵詞:儒家文化;創(chuàng)造力;積極影響;消極影響
中圖分類號:G02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21-0090-02
文化作為物質(zhì)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現(xiàn)實(shí)的活動,無論是思想上還是行為上的。創(chuàng)造力不僅僅體現(xiàn)了人的思維特性,而且在行動中彰顯。作為中華文化中主流的儒家文化與創(chuàng)造力之間在功能上的關(guān)系是很值得探討的;儒家文化的“基因”如何一步一步地成就中華五千年的文明,而后又導(dǎo)致了后期的落后挨打的局面也是令人深思的。
一、創(chuàng)造力的理解
什么是創(chuàng)造力?德國的海納特在《創(chuàng)造力》一書中認(rèn)為,“從詞源上來看,創(chuàng)造力是在原先一無所有的情況下,創(chuàng)造出新的東西”[1]14。這個定義基本體現(xiàn)出了創(chuàng)造力的實(shí)質(zhì),但是卻沒有展現(xiàn)其具體的內(nèi)容。《辭海》中對創(chuàng)造力的解釋是:“對已積累的知識和經(jīng)驗進(jìn)行科學(xué)的加工和創(chuàng)新,產(chǎn)生新概念、新知識、新思想的能力。大體上由感知力、記憶力、思考力、想象力四種能力所構(gòu)成。”[2]517筆者認(rèn)為《辭海》給出的定義是比較確切具體的。
二、儒家文化對創(chuàng)造力的積極影響
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流能夠“屹立”千年而不曾中斷,這其中的原因想必大多數(shù)人并不知曉。國學(xué)大師梁漱溟就曾指出:“中國文化在其綿長的壽命中,后一大段(后兩千余年)殆不復(fù)有何改變與進(jìn)步,似顯示其自身內(nèi)部具有高度之妥協(xié)性、調(diào)和性,已臻于文化成熟之大成者。”[3]8的確,正是儒家文化的早熟,成就了其歷史的“不衰”。這種早熟,是理性的早熟,使中國人過早地認(rèn)識到“和”的重要性。即使“人各有志”,也可以“和而不同”。“和”的思想為形成“大一統(tǒng)”的文化傾向奠定了文化基礎(chǔ);因為,統(tǒng)一而不能做到和而不同,必定會再次迅速分裂。在整個中國歷史中,一統(tǒng)的時間要長于分裂的時間,而統(tǒng)一是穩(wěn)定的前提。此外,儒家文化提倡人倫、尊崇禮樂;這些被后來的儒家逐漸發(fā)展成倫理綱常,更進(jìn)一步維護(hù)了社會的穩(wěn)定。如此,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就為發(fā)展創(chuàng)造力打下了堅實(shí)的社會基礎(chǔ)。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首先有利于物質(zhì)生產(chǎn),有了物質(zhì)生產(chǎn)的順利進(jìn)行,在此基礎(chǔ)上的生產(chǎn)經(jīng)驗的總結(jié)才有可能。總結(jié)、改進(jìn)生產(chǎn)技術(shù),創(chuàng)造、發(fā)明生產(chǎn)工具,如此便成就了中國歷史上長達(dá)千年而遙遙領(lǐng)先的物質(zhì)文明。“四大發(fā)明”最能體現(xiàn)中國古代的創(chuàng)造力了。
物質(zhì)的發(fā)展改善了人們的基本生活,所謂“倉廩實(shí)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樣以后人們才有相對更多的閑暇時間去從事藝術(shù)創(chuàng)作。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正體現(xiàn)了中國在文學(xué)藝術(shù)方面的創(chuàng)造力。
儒家文化是極具包容性的文化。古人常講“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即便開始是敵人,最終也可能被我同化,成為我們的人。“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不管其他民族的文化如何入侵,儒家文化始終能夠吸收外來文化的合理內(nèi)核,為我所用,不斷充實(shí)自己。不同的文化碰撞交融,對于知識的分享與傳播,對于智力的開發(fā)都是很有益的,當(dāng)然也是有益于創(chuàng)造力的。比如:儒家就融合了佛家和道家的某些精神,不斷創(chuàng)新、與時俱進(jìn),提升了儒家的文化內(nèi)涵與境界,難道這里沒有創(chuàng)造嗎?此外,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產(chǎn)生了有別于印度“大乘佛教”而和儒家一樣入世的“小乘佛教”,這也是包容文化創(chuàng)造力的體現(xiàn)。在這樣理性、成熟、包容的儒家文化的影響下,中國古代在天文、地理、文學(xué)創(chuàng)作等各個領(lǐng)域都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可以說不勝枚舉。
常言道:“此一時,彼一時”,到了清朝末年以后儒家文化面對西方文化的強(qiáng)勢入侵已經(jīng)無能為力了。這說明潛伏在儒家文化內(nèi)部的某些消極作用已經(jīng)顯現(xiàn),并阻礙了中國的發(fā)展,使中國落后西方,所以才有百年的屈辱歷史。
三、儒家文化對創(chuàng)造力的消極影響
(一)“仁”“義”“中庸”的理念對創(chuàng)造力的消極影響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愛人。繼續(xù)對孔子“仁”的思想進(jìn)一步發(fā)揮,孟子提出了,人之初性本善的認(rèn)識論。漸漸地,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古人非常重視德性修養(yǎng),都以正人君子的標(biāo)準(zhǔn)來要求自己。對人對事,人們強(qiáng)調(diào)“三省吾身”,常常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發(fā)生矛盾習(xí)慣從自身找原因,而不總是向外苛求他人。這種仁的理念有益于人際關(guān)系的和諧,但過于關(guān)注人就會在某種程度上削減對自然的關(guān)注,對外在的追問。長久以往,我們對于客觀世界的把握能力就會停止不前,也就會限制創(chuàng)造力的發(fā)揮。
所謂“義”可以理解為韋伯那里的“價值理性”,那么“利”即是“工具理性”。儒家文化更關(guān)注“價值理性”,孟子說:“生我所欲也,義我所欲也,兩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因此我們沒有那么功利,所以在改造自然的魄力上,沒有西方那么徹底,外在的創(chuàng)造力也就受到了制約。工具理性把人當(dāng)成手段,為了達(dá)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總是考慮利益的最大化,這樣也最能激發(fā)人的創(chuàng)造力。
“中庸之道”,就是為人處世不偏不倚,明白事情總是過猶不及。這種處世方法某種程度上把握了自然的本質(zhì)。可是如此的處世方式很容易產(chǎn)生對知識的不求甚解。這種態(tài)度不能把對知識的渴望發(fā)揮到極致,容易把好奇心給抹殺了。果真,不走極端、不敢追問,如何能有更多新的發(fā)現(xiàn)。殊不知正是“極端”才產(chǎn)生了德國哲學(xué)的輝煌,尤其是近現(xiàn)代最偉大的哲學(xué)家大部分都出自德國;因為德國人只要一談問題就要上升到哲學(xué)的高度,甚至常常無窮地追問到本體論的層面。由此可見德國人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執(zhí)著與認(rèn)真。文化基因一旦如此這般,就會在方方面面體現(xiàn)出它的影響。比如:德國人在制造技術(shù)上的精益求精終于成就了德國的高端制造的世界性地位。德國的這種在制造上面的創(chuàng)造力想必國人無人不知。與之相反,國人卻總是偏愛“差不多”的中庸思想,正是如此我們在制造業(yè)上的創(chuàng)造力才很難彰顯。
“中庸”的理念直接產(chǎn)物就是“謙虛”。當(dāng)謙虛成為美德同時也意味著某種程度的個性不張。不張的個性很難產(chǎn)生懷疑精神,而懷疑精神是破除迷信的關(guān)鍵。要知道“不破不立”,創(chuàng)造就是“立”,沒有懷疑精神去“破”,哪有創(chuàng)造的“立”。而事實(shí)上,儒家文化到后期甚至形成了“三綱五常”封建倫理道德,提倡“三從四德”,更是限制了人的個性和創(chuàng)造力的發(fā)展。
(二)家庭倫理與耕讀方式對創(chuàng)造力的消極影響
從西周建立分封制的宗族國家之后,家族在整個封建社會都是最重要的一個單位。國法、家規(guī)在維護(hù)社會穩(wěn)定方面起到了同等的作用,可以說并行不悖。錢穆先生認(rèn)為:家族制度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柱石。就連德國古典哲學(xué)家黑格爾也曾斷言:“中國純粹建筑在這一種道德的結(jié)合上,國家的特性便是是家庭孝敬。”[4]65所以中國自古以來是家國不分的。但是,在家庭中講求的倫理過于強(qiáng)調(diào)遠(yuǎn)近親疏。這樣的家的概念,就必然預(yù)示著某種程度的“閉關(guān)鎖國”,所謂“家丑不外揚(yáng)”,便是此理。中國自古以來,很多經(jīng)驗、技巧都是家傳的,幾乎不外傳。這很不利于技術(shù)、知識的保存、推廣與創(chuàng)造,最終導(dǎo)致很多技術(shù)、文化成果失傳:神醫(yī)華佗的重要的醫(yī)學(xué)著作《青囊書》已經(jīng)失傳,諸葛亮的“車水馬龍”也難以復(fù)原,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我國是典型的以農(nóng)耕為主的國家,自給自足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一直以來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自古以來重農(nóng)抑商,認(rèn)為農(nóng)業(yè)是本業(yè),而商業(yè)是末業(yè)。這樣長此以往就限制形成廣闊的統(tǒng)一大市場;到后期又閉關(guān)鎖國,因此海外市場也沒有了。沒有廣泛的市場交換也就阻礙人們信息的充分交流。要知道信息是知識的基礎(chǔ),知識是創(chuàng)造力的源泉之一。更重要的是,即使像四大發(fā)明這樣的技術(shù)產(chǎn)生了,如果沒有向外拓展的市場需求的誘導(dǎo)也很難有在此基礎(chǔ)上的進(jìn)一步創(chuàng)新。比如指南針西方用于航海,而我們用于“風(fēng)水”;西方用火藥研制武器,而我們卻只會制作鞭炮。
說到讀書,中國人自古讀的是圣賢之書,學(xué)的是孔孟之道。之所以讀這些書主要是為了鞏固統(tǒng)治以及維護(hù)社會的穩(wěn)定。儒家經(jīng)典“四書五經(jīng)”講的多是如何“做人”的學(xué)問,關(guān)注人際社會而不太精通自然學(xué)問。人際關(guān)系是研究透了,所以人們精于世故人情,可是對自然科學(xué)的了解卻是大大不足。為了在科舉中奪得頭籌,大部分最優(yōu)秀的人才,投身于世故的舊思想、舊學(xué)問,可以說浪費(fèi)了大批的最優(yōu)秀人力資源,極大地減少了最具創(chuàng)造力的主體。在考試的內(nèi)容上多是“本本主義”,并不太注重實(shí)踐的知識,甚至鄙視勞動實(shí)踐。因為儒家認(rèn)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不注重實(shí)踐,創(chuàng)造力談何容易。
(三)儒家文化的思維模式對創(chuàng)造力的消極影響
“孔子只是一個實(shí)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學(xué)是一點(diǎn)也沒有的――只是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xùn)”,黑格爾的話似乎是在批評貶低孔子[5]119。但是,他所指出的內(nèi)容無疑是對的。西方哲學(xué)思考喜歡用概念、知性范疇、邏輯來闡述分析問題;中國哲學(xué)理解、分析問題憑借的是直觀的生命體驗而非邏輯。儒家的這種思維方式往往能夠直達(dá)知識本身。可是,沒有理智的分析過程,這種知識就只能靠人的悟性了,中國文化早熟也正體現(xiàn)在此。這種早熟早期有優(yōu)勢,但是到后期便成了劣勢。要知道沒有邏輯的演進(jìn)過程,直接一步登天,雖然快,但畢竟不穩(wěn)。就像蓋房子,沒有穩(wěn)固的根基作為基礎(chǔ),自然是不能穩(wěn)固的。所以,盡管開始我們成就非凡,到后來就一敗涂地了。西方人雖然晚熟,可是在堅實(shí)的邏輯分析基礎(chǔ)之上終于建立了現(xiàn)代科學(xué),人的創(chuàng)造力得到了充分的發(fā)揮和利用。從此“分析科學(xué)”戰(zhàn)勝了綜合的理性,中國漸漸開始落后西方了。
“風(fēng)水輪流轉(zhuǎn)”,雖然西方文化在創(chuàng)造力方面,在近現(xiàn)代表現(xiàn)出暫時的優(yōu)勢。但是,西方文化那種內(nèi)在的“沖突”“異己”的特性終究不能取帶崇尚和諧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優(yōu)秀成分在不久的將來必定再次顯現(xiàn)其在創(chuàng)造力方面的積極影響。
參考文獻(xiàn):
[1][德]海納特.創(chuàng)造力[M].陳鋼林,譯.北京:工人出版社,1986.
[2]夏征農(nóng).辭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
[3]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