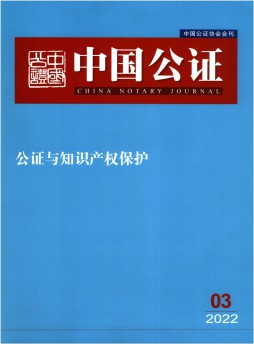民事法律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民事法律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一、因果關系的理解
因果關系是一個哲學概念。無論是在自然界,還是在人類社會中,任何一種現象的出現都是由一種或幾種現象引起的。引起某種現象產生的現象稱之為原因,被某種現象引起的現象稱之為結果。客觀現象之間的這種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就是因果關系。侵權民事責任中的因果關系是特殊的因果關系,它是哲學上因果關系范疇在民事法律上的運用。有學者認為侵權民事責任中的因果關系就是研究特定的損害事實是否系行為人的行為必然引起的結果,如果是,則具有因果關系,否則,就沒有因果關系。這種認識有失全面,原因與結果之間不僅僅是必然的引起關系,還存在一種或然的,或者說是間接導致關系。甲與乙系老戰友,久別重逢。甲喜悅之余擂了乙一拳,恰好引發了乙的心臟病導致乙死亡。甲的行為能夠必然引起乙的死亡嗎?不能。我們是否能夠就此認定甲的行為與乙的死亡沒有因果關系?也不能。因此說,侵權民事責任中的因果關系,既包括必然的因果關系,也包括偶然的導致關系。既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也存在間接的因果關系。
1、因果關系中的原因
侵權民事責任因果關系中,究竟什么樣的因素才是原因,存在眾多的認識。過錯原因說認為侵權民事責任中的因果關系就是過錯與損害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只有存在過錯,行為人才對其造成的損害負責,才承擔賠償之責。反之,即使行為人的行為造成了損害,行為與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若行為人沒有過錯,亦不承擔賠償責任。行為原因說認為,民法中的因果關系是指行為人的行為及物件與損害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只有行為才能作為因果關系中的原因。違法行為原因說認為,侵權民事責任中的因果關系是指違法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的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違法行為才是因果關系中的原因。還有侵權行為原因說、被控行為原因說等等。筆者認為,因果關系是一種客觀的、事實上的聯系,與社會主體的主觀意志。通常所稱的過錯包括故意或者過失,是主體主觀意志的體現。如果把作為人的主觀意志體現的過錯作為因果關系的原因來考察,會不會得出這樣的一個邏輯:“某甲想傷害某乙某乙有受傷害的事實某甲故意傷害的過錯引起了某乙受傷害"?顯然不成立。事實是客觀的,只能由客觀現象引起。作為客觀事實的損害也只能由客觀情況引起。因此,過錯不應當成為侵權民事責任因果關系中的原因。而違法行為原因說已經能夠從因果關系是客觀事物之間的聯系這一角度考察因果關系的原因,符合民法上因果關系通常理論認識,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將違法行為確定為因果關系的原因大大限制了原因的范圍,不符合客觀實際,在實踐中也難以操作。首先,對于侵權民事責任中的因果關系,我們考慮的是引起結果發生的眾多原因中主要的、異常的因素。火災的發生肯定是存在氧氣燃燒的原因,但這與法律無關,我們只考慮其中的異常的情況,是放火、失火還是自燃。同樣,如果將違法行為作為侵權民事責任因果關系中的原因,我們只需要審查損害事實是不是行為引起的,這個行為是不是違法的,而不需要審查其他的任何因素。歸根結底,就是在審查行為是否違法的問題。這樣認定損害的原因顯然有失偏頗,不夠全面,結論是:只有違法的行為才能是損害發生的原因。而在實際的操作中,我們會不難發現造成損害事實發生的原因很多,不可能僅僅是違法行為。其次,違法的情形難以認定。民事法律制度中,通常是權益性的規定較多,禁止性的規定很少,也很少有屬于“違法"這一序列的明確行為規定。這樣,如果將違法行為作為因果關系的原因,必然是大大限制了因果關系中的原因范圍。而我們在很多時候會將一些僅僅屬于疏忽大意、過于自信等情況但又明顯引起損害事實發生的行為作為原因,不適當地擴大了違法行為的認定范圍,混淆了違法與過錯的關系。甲誤將過期的酸奶作為新鮮的給同事乙飲食,造成乙生病住院。甲違法嗎?不違法,但其行為與乙生病住院這一損害事實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因此,筆者認為,侵權民事責任中的因果關系應當是一種行為(既包括積極的作為形式,也包括消極的不作為形式)與損害事實的關系,即使是在由于法律的規定責任人必須對他人的相關行為承擔責任或對事件負責的情況下,也是由于行為人的行為引起了損害后果或者是責任人未盡義務的不作為造成了損害后果。在該因果關系中,原因和結果都是特定的,行為是原因,損害事實是結果。這樣的認定不會與民事責任的構成相互沖突。有學者認為,否認違法行為作為損害事實的原因,就是否定違法行為是侵權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首先,法律沒有明確規定違法行為是侵權民事責任的必要構成要件。其次,即使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隱含了這樣的觀點,行為是因果關系中的原因與違法行為是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也是一致的。權利人向責任人主張損害賠償必然是因為自己的合法權利遭受侵害(如果不是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而主張,必然會被法院駁回請求),既然行為人的行為侵害了他人受法律保護的合法權益,說明該行為本身就是一種違法的行為,而無須畫蛇添足地說明違法行為才是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當然,是否承擔責任,還要考慮行為人的過錯和歸責原則的規定等眾多因素。
2、因果關系中的結果
在侵權民事責任因果關系中,一般都認為損害事實是因果關系中的結果。該損害事實包括物質損失和精神損失兩個部分。這里值得注意的有兩點,其一,法人也存在精神損害賠償問題。我國民事法律既規定了公民的各種人格權和人身權,同時也規定了法人的名稱權、名譽權等權利。應當來說,建立在法人人格基礎上的法人名稱權、名譽權受到侵害的,也存在精神損害賠償的問題,但在司法實踐中并沒有得到認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10條第4款規定:“公民、法人因名譽權受到侵害要求賠償的,侵權人應賠償侵權行為造成的經濟損失;公民并提出精神損害賠償要求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侵權行為的具體情節、給受害人造成精神損害的后果等情況酌定。"從該規定可以看出,法人因侵權造成的經濟損失可以向侵權者提出賠償請求,但可以提起精神損害賠償請求的只能是公民個人,法人不具有這樣的權利。第二點值得注意的是,公民因侵權造成的死亡賠償金和殘疾賠償金已經列入物質損害賠償的范圍,不再僅僅是精神損害。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司法解釋的方式確立了死亡賠償金和殘疾賠償金物質損害的地位,該規定與我國《國家賠償法》對死亡賠償金性質的規定相一致,符合民法的原理,也體現了法律規定的一致性和嚴肅性。但是該規定中死亡賠償金的計算標準有有所不妥,其劃分了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不同標準,未能體現對公民民事權利能力喪失的平等保護。
二、因果關系的認定
對于侵權民事責任因果關系的分析和認定,應當分兩個步驟進行:
首先,確定行為人的行為或者依法由責任人承擔責任的事件或行為是否在事實上屬于損害事實發生的原因,即事實上的因果關系。
其次,確定事實上屬于損害事實發生原因的行為或事件在法律上是否能夠成為責任人對損害事實承擔責任的原因,即法律上的因果關系。
1、事實因果關系的確認
確認某一行為是不是某一損害事實上的因果關系,通常可以通過以下幾種規則予以確定。第一種是必要條件規則,其基本方式是“要是沒有"。如果沒有行為或事件的出現,就不會有損害事實的發生。行為或事件是損害發生的必要條件,凡屬于損害事實發生的必要條件的行為或事件均系事實因果關系中的原因。第二種規則是實質要素規則,即某種行為或事件雖然不是損害發生的必要條件,但卻是足以引起損害發生的充分條件,就構成事實上的因果關系。該認定規則不是對必要條件規則的排斥和修正,而是對它的補充,彌補了必要規則的不足。第三種是因果關系的推定規則。在某些情況下,運用通常的規則無法證實事實因果關系,法律規定了特殊的認定規則,這里包括因果關系的推定規則。該規則要求責任人舉證證明應當由其承擔責任的行為或事件不是造成損害結果發生的原因,如果不能舉證的,則認定有事實上的因果關系。經常列舉的例子,甲乙都有從樓上往下扔啤酒瓶的行為,其中的一個啤酒瓶造成了丙的傷害,但不能區分是哪一個啤酒瓶造成的,則認定甲乙均承擔責任,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共同危險行為。在該損害事實因果關系認定的過程中,我們采取了因果關系的推定規則。同樣的,筆者認為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條的規定也是采用了因果關系的推定規則。該條認為“……如果能夠證明損害是由受害人自己故意造成的,不承擔民事責任。"除了能夠證明損害是由于受害人自己故意造成的,否則就認為行為與結果具有因果關系,侵權人或相關事件及行為的責任人即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司法實踐中也經常對因果關系進行推定。有一案例:某小學三年級學生在學校期間被發現跌倒在樓梯井底部,沒有證據證明該學生是如何受傷的。經鑒定,結論是該學生高空墜落的可能性較大,則法院推定該學生系從樓梯井上部墜落,遂認定了學校未盡安全義務的不作為與損害事實的發生具有因果關系,判決其承擔了一定的責任。這也是適用因果關系推定的結果。
第2篇
關鍵詞:無紙化/證券交易/民事法律關系
無紙化證券是電子科技在證券市場不斷發展的產物,它是證券登記結算機構或者證券公司計算機系統處理的電子簿記系統內反映證券持有狀態的電子數據信息。投資者通過其在證券登記結算機構或證券公司開立的證券賬戶持有證券,并通過該賬戶進行證券交易和轉讓。相比傳統的有紙化證券,證券持有人原先對紙面證券的支配,演變為通過證券賬戶對其中的電子記錄或者電子數據的支配。目前,我國資本市場的市值已在30萬億元左右,證券賬戶總數超過1.4億。2007年,滬深證券交易所日均證券過戶總金額達2000多億元。也就是說,我國單在證券市場就有30萬億元左右的財產權益都是以無紙化的形式存在,而且每天的流轉總量超過2000億元。可見,以無紙化方式存在的證券財產已經成為社會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黨的十七大也提出的“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的重要途徑。
從本質上說,因無紙化證券權益確認和流轉發生的法律關系屬于民事法律關系的范疇,但是,由于權益載體“無紙化”的特殊物理環境,“權利表現為數字或電子符號;而這些符號又記載于特定的密碼賬戶下面。”[1]上述變化客觀上使得以有體物和以紙面憑證為載體的權利為考量對象的傳統民事法律適應不了實踐的客觀需要,有關證券權利的歸屬、變動、流轉和實現等的相關制度和規則要不存在一些難以適用的情形,要不就是缺少相應的明確規定。無紙化條件下,“電子證券法律規則的缺失對于所有證券市場的參與者而言都是一種不確定性,所有證券市場的參與者將無法按照法律規則明確相互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2]由此可見,以促進證券交易效率提高和交易成本降低為目的的證券無紙化給證券的發行、持有和交易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這種變化對傳統民事法律制度的挑戰是全方位的,亟需從無紙化條件下證券民事法律關系的特殊性出發,抽象出專門的規則和制度,完善《物權法》、《擔保法》、《合同法》、《破產法》、《證券法》等相關民商事法律,明確界定和規范無紙化證券民事權利和義務關系。
一、各類證券賬戶的性質和功能需要法律明確規定
證券賬戶是用于記錄投資者持有證券的余額及其變動情況的載體,證券賬戶記載的內容既是證券權益確認和流轉的基礎和前提,又是證券權益確認和流轉的結果和目標。無紙化證券與證券賬戶不可分離,投資者對證券的持有只能通過控制證券賬戶來實現,不同的證券賬戶所代表和反映的證券權益也不相同。證券賬戶相當于投資者的“證券存折”,用于記錄投資者所持有的證券種類、余額及變動情況。證券賬戶由證券登記結算機構以投資者本人名義為投資者開立,實踐中多由證券公司等開戶機構開戶。證券以紙質憑證存在的條件下是不存在證券賬戶的,投資者只要持有合法取得的證券,就可以對證券進行處分,并擁有證券權利(質押、接受分紅派息及投票權等);但無紙化條件下這一切權利的行使都需通過證券賬戶來進行。證券賬戶在無紙化證券的市場中扮演著首要角色,可以說,離開了證券賬戶,無紙化證券交易便無法實現。
證券市場目前存在多種賬戶類型,如普通證券賬戶、名義持有人(nominee)賬戶、融資融券賬戶、證券交收賬戶、專用清償賬戶、基金賬戶、定向資產委托管理賬戶等,由于法律對于各類證券賬戶的性質、功能、各種證券持有關系中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等沒有明確規定,實踐中暴露出來的矛盾和問題典型地反映出直接持有和間接持有體系的不同法律效果背后所依托的基礎法律制度的差異:直接持有依托“一物一權”的傳統大陸法系物權制度,是投資者同時作為名義上的所有者直接持有證券的體制;間接持有是指投資者將持有證券交付一個或多個中間機構(證券公司),后者再將投資者交付的證券交存到中央證券存管機構(CSD),發行人股東賬戶登記的證券所有者是最后的中間機構,CSD在登記機構取得股東或債權人的法律地位。
在大陸法系“一物一權”的法律語境下,賬戶登記記載的權利人在法律上被推定為真正的權利人,投資者直接對發行人擁有請求權,被直接登記為其持有證券的所有權,相應地取得股東或債權人的地位。而名義持有人(nominee)賬戶的真正投資者的名稱是不顯示在賬戶名稱中的,也不顯示在股東名冊上,因此這類賬戶的實際受益人的證券權益如何確認在法律層面也缺乏明確規定。有觀點認為,間接持有依托“雙重所有權”的信托制度,“間接模式實際上是信托方式,證券被登記在經紀-交易人、銀行或專門存管人賬戶上,該中介機構作為證券的注冊持有人或在冊所有人(recordowner)擁有法定所有權(legalowner);而投資者作為最終持有人或受益人(beneficialowner)擁有收益權(beneficialownership)。”[3]一旦名義持有人和實際受益人對證券權屬發生爭議時,這一問題便凸顯出來,實踐中發生過投資者根據證券價值的漲或跌來選擇主張所有權或是主張債權的案例,也成為間接持有制度的難點之一,對于如此重要的民事法律關系問題,我國僅有中國證監會的部門規章《證券登記結算辦法》第18條有相關的原則規定“證券應當記錄在證券持有人本人的證券賬戶內,但依據法律、行政法規和中國證監會的規定,證券記錄在名義持有人證券賬戶內的,從其規定。”而名義持有人制度下,投資者和發行人之間,以及投資者和中介機構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性質的法律關系?投資者對于無紙化證券的權利是“純粹的契約性權利”、“共有權”、“信托所有權”還是一種完全不同于傳統權利狀態的“證券權益”?都沒有做出具體明確的規定,這種法律規定的空白狀態,必然會影響到證券市場的穩定運行和創新發展。“投資者的權利性質、權利的行使方式以及保護投資者權益的具體措施必須明確。否則,因為立法不明確所造成的法律風險將會極大地阻礙證券市場的發展。”[4]
二、物權法律制度需要明確證券權益保護的特殊規則
證券無紙化后,投資者對證券的所有權不再依據持有實物證券或者證券上的記名,而是以證券登記機構的電子簿記記錄為依據,體現出非流動性的特點,類似于不動產物權登記;同時,以電子數據形式記載的證券權利,又具有高流動性的特點,類似于動產物權。證券交易的實際情況是,證券的交收不再需要交付證券或者變更證券上的記名,而是由證券登記機構對電子簿記系統中的證券賬戶記加或者記減記錄而做出變更。顯然,由于無紙化證券的特殊存在形式,其權利的歸屬依賴動產權利規則或不動產權利規則存在難以適用的情形。
;
無紙化證券的權屬確認和變動是通過證券登記來完成的。而無紙化證券的登記不同于物權登記,它是與證券賬戶結合在一起的,登記可以產生證券權利,如證券發行采用無紙化方式,登記即表明取得證券權利,而無紙化證券的登記又沒有發放權利證書,這都與物權登記有所不同。不動產物權登記著眼于登記機構對于不動產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的確認,是不動產物權變動的公示形式。而證券登記由于簿記記錄的特殊性,往往在過戶行為的同時發生,不存在權利變動和登記行為的分別實現。此外,從法律效力來看,證券登記的法律效力,不僅是對證券權利狀態的記載和確認,即通過證券登記,可以確認證券合法持有人和處分權人的資格,也可以標明該證券上的權利限制狀況,而且還體現為對證券行為狀態的記載和確認,如要約收購登記,以判斷證券行為結果是否確定和符合規則要求。但就證券登記結算機構進行的證券登記行為,是否可以作為產生無紙化證券權益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的法律后果的行為,法律上并沒有明確規定。證券登記的登記事項、登記程序、登記職責等也缺乏法律的明確依據。《證券法》第160條第二款的規定“證券登記結算機構應當根據證券登記結算的結果,確認證券持有人持有證券的事實,提供證券持有人登記資料……”。該條規定并未明確證券賬戶的登記記錄具有確認證券權益歸屬的效力。而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的《證券登記規則》作為商事特別規則規定了登記是確權依據,但由于其層級較低,司法實踐中往往不予認可其效力,一些法官從傳統物權法的概念原則出發,認為股票所有權的判斷并非以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的登記為準,證券登記是持有登記而非所有權登記,不能作為股票所有權的唯一判斷依據,由此對無紙化證券交易制度造成了相當的影響。三、合同法律制度應當完善集中交易機制的規范內容
在無紙化證券交易環境下,上市證券在集中交易場所以匿名的,由中介人(證券商)介入、“多對多”的電子化方式集中撮合成交。賣出證券將經由賣出客戶證券賬戶,賣出方證券公司證券交收賬戶、證券登記結算機構集中交收賬戶、買入方證券公司證券交收賬戶和買入客戶證券賬戶等五類證券賬戶實現證券權益的流轉。在這過程中,共同對手方(CentralCounterParty,CCP)制度是實現證券交易結算的重要制度基礎。我國證券市場實踐中,證券登記結算機構事實上擔當著絕大部分交易品種和交易方式下的中央對手方,包括以集中撮合方式進行的A股、國債、企業債、回購交易、封閉式基金、ETF、LOF等。共同對手方制度的要義在于,登記結算機構介入證券交易買賣雙方之間,成為“買方的賣方”和“賣方的買方”,這種交易模式完全不同于一對一的傳統交易方式。這一制度要求結算機構作為共同對手方,介入賣買雙方的合同關系,成為所有結算參與人唯一的交收對手。“中央結算機構與參與人的債權債務關系是一個不同于原參與人之間的新的債權債務關系,這兩個債權債務是獨立的,這不僅是因為當事人不一樣,更主要的是因為債權債務關系基于不同的法律關系,參與人之間債權債務基于分別代表其客戶的證券買賣協議;而中央結算機構與參與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基于中央結算規則,如果發生糾紛,依據的不是證券買賣協議,而是按照中央結算規則產生的清算表。”[5]
共同對手方制度的核心內容是責任更替和擔保交收。責任更替的要義在于原來買賣雙方達成的合同被雙方分別以結算機構為共同對手方的兩個新的合同所取代,買賣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為共同對手方所承接,當事人只與結算機構一個對手方發生權利義務關系,進行資金和證券的交收。關于中央對手方的形成方式,英美法系國一般采取“約務更替”(novation)制度,也稱為“合同更新”。我國是大陸法系國家,合同法中沒有類似制度,相似的制度是《合同法》第88條關于“當事人一方經對方同意,可以將自己在合同中的權利和義務一并轉讓給第三人”的規定,但考慮到證券交易數量極大,且在瞬間完成,證券公司間達成的合同,無法依據《合同法》第88條,經過雙方同意,將合同權利義務一并轉讓給結算公司。同時,根據共同對手方制度中的擔保交收制度,共同對手方承擔的履約義務并不以任何一個對手方正常履約為前提,即使買賣中的一方不能正常地向共同對手方履約,作為共同對手方的登記結算機構也應該首先對守約一方履行交收義務,然后再根據規則處置違約一方的資產和擔保物,或者向違約方追索等辦法彌補對手方違約造成的損失。由此可見,共同對手方(CCP)結算制度要求有一套完全不同于《合同法》等法律規定的合同履行規則和制度,現行法律難以為登記結算機構成為共同對手方制度提供合理解釋。同時,《證券法》也沒有明確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的“共同對手方”地位,需要將現有部門規章《證券登記結算管理辦法》中規定的共同對手方制度提升為法律層面的規定。
四、擔保法律制度需要體現證券交收擔保機制的特殊性
金融之本在于資金的融通和流動,而要保障資金融通和流動的順利實現,則離不開有效的擔保法律制度。在無紙化證券交易過程中,交易一方或各方不能按照約定條件足額、及時履行交收義務,其負面效果不只及于傳統交易中的對方,由于實行中央對手方(CCP)交易制度,個別當時人的違約風險往往會演化成系統性的證券交收延遲或交收失敗,在這里,違約風險呈明顯的“敞開性”特點。防范和管理結算風險決定了證券登記結算系統的穩定連續運行,決定了證券交易能否得以最終完成,也決定了整個證券交易系統的安全。在證券交易結算中引入全面的擔保機制,將最大限度的防范結算風險。無紙化證券交易條件下的“擔保體系并不限于一般擔保法意義上的擔保,指為確保證券交易結算的順利完成、確保證券與資金的交割交付而制定的有關機制,特別是在交收違約發生之后為確保交收完成的保障機制,這種機制的核心要素在于在義務人的財產之上設置了某種他人權利,特別是中央登記結算機構的權利。……所以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擔保機制并非為了中央結算機構自身利益,甚至可以說在結算關系上中央結算機構沒有自身利益。”[6]事實上,建立在一對一的傳統交易模式基礎之上的擔保法律制度,無法滿足無紙化證券集中交易結算對于建立一攬子擔保機制的需要,現行擔保法律制度并沒有表現出對于無紙化環境的完全適應性。
一是關于擔保的成立強調訂立書面的合同。而在集中交易的證券領域,書面合同的雙方合意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無紙化證券的交易結算關于擔保的設立大多以業務規則先行的方式解決。當事人一旦進入交易,即被視為接受交易結算規則,而無需另行簽訂單個的書面合同。因此有必要以專門的法律規定來確認以規則方式解決一攬子擔保成立的效力。
二是擔保的具體實現形式偏于單一。《物權法》僅規定質押以登記方式生效,而在當前的證券交易結算實踐中,不同的交易品種的擔保實現方式有一定程度的差異,有過戶、有登記、有控制、有提交。如舊國債回購交易中,以回購登記為擔保設立要件;而新回購交易中則為擔保國債轉入質押庫為擔保設立要件;交收擔保品則以擔保品提交入庫作為擔保成立要件;對于存在自營及經紀業務的結算參與人,客戶資金交收賬戶不足時,登記結算機構可以直接動用自營賬戶內證券完成交收。因此在當前的實際證券交易結算中,擔保物權具體實現形式需要有相應法律的專門解釋規定。
三是沒有規定讓與擔保制度。讓與擔保是適應商事實踐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一種法律制度。在證券交易領域,讓與擔保以證券轉入擔保權人證券賬戶作為證券擔保權益生效要件,轉入擔保權人證券賬戶的證券歸屬擔保權人,若擔保人到期履行債務,擔保權人保證返還同質同量的證券財產。這種新型的非典型擔保物權在金融創新實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期貨交易管理條例》確立了有價證券充抵保證金制度,但由于缺少讓與擔保制度,影響到該項制度功能的發揮。中國證監會的《證券公司融資融券試點管理辦法》基于實踐的需要規定了相似性質的融資融券擔保制度,但由于缺乏上位法的支持使其合法性受到質疑。我國著名民法學者王利明教授認為,雖然《物權法》未規定讓與擔保制度,但是,目前開展的融資融券業務并不會受到影響。當事人可以根據《信托法》確立法律關系。但從為證券業金融創新提供制度基礎的角度,他也指出,“在條件成熟的時候,也可以制定特別法來確立讓與擔保制度。”[7]與此相關聯的是關于禁止流質的規定如何與應證券市場的發展和創新的需求相協調,使之更加有利于市場交易手段的完善和業務模式的拓展。事實上,已經有部門規章層級的《證券公司股票質押貸款管理辦法》突破了原《擔保法》和《物權法》的限制,質權人(銀行)可以在股票市值降至平倉線時,出售質押股票。但直接轉移擔保品以償債規定與我國現行物權法規定的禁止流質原則有所不符。
五、破產法律制度需要考慮證券清算交收的實際需要
《破產法》作為處理破產清算條件下特殊債權債務關系的專門法律,基于債權人公平受償的基本法律價值取向,規定在破產程序啟動后,不能有缺乏法律依據的個別清償行動。破產程序一旦開始,即使是擔保債權人也不能獨自行使其擔保債權。具體到強調安全與效率并重的證券市場,按照無紙化證券特殊交易規則要求履行職責的中央登記結算機構,會因為破產法缺乏特別的規定而面臨相當大的法律風險。
一是清算交收系統的優先性應當予以明確。清算交收系統履約優先原則是國際上對清算交收系統保護的基本原則之一。如我國香港地區及歐盟均規定,清算交收系統相關規則優先于破產法律適用。“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盡管具有債權人的法律地位,但并沒有獨立的利益,證券登記結算機構債權的實現維護的是整個證券市場的結算安全和全體結算參與人的利益。因此,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的債權應優先于其他債權實現。”[8]企業破產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后,債務人對個別債權人的債務清償無效”。這可能成為證券登記結算機構在結算參與人進入破產程序后享有優先地位的障礙,不利于清算交收系統的安全和穩定。證券登記結算機構作為共同對手方,破產結算參與人在結算系統透支時,證券登記結算機構墊付資金完成已達成交易的交收,而該部分墊付的資金來自全市場結算參與人的資金。因此,如果不允許證券登記結算機構對擔保物行使優先受償權,侵害的將是全市場結算參與人的利益,違反公平原則。因此,清算交收系統的優先性是否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得到體現:一方面,結算參與人破產時,證券登記結算機構有權依據業務規則強制要求結算參與人完成進入破產程序前后已達成交易的交收,證券登記結算機構不應受到《破產法》自動中止原則的影響,而且即使結算參與人未提供擔保,結算參與人的破產財產也必須優先用于履行交收義務,另一方面,結算參與人進入破產程序后,在債務人財產的分配順序中,應當賦予證券登記結算機構作為債權人的優先地位或者法定的優先清償順序,證券登記結算機構對依據業務規則強行留置的違約交收證券和結算參與人提交的擔保物有優先受償權,且有權直接依據業務規則對擔保物進行處分。這種優先權應當得到法律的確認,證券登記結算機構可直接依據業務規則行使這種權利,而無需征得法院事先同意。
二是破產管理人的撤銷權應受限制。《企業破產法》第31條賦予了破產管理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決定是否解除破產申請受理前成立而債務人和對方當事人均未履行完畢的合同的權利。然而,此項規定與國際通行的無紙化證券交易最終性原則存在一定的沖突。特別是,當作為結算參與人的證券公司破產時,執行《破產法》的有關規定,就可能影響集中交易和多邊凈額結算秩序,引發系統性風險。因此,對于證券交易所市場已達成的集中交易和已進入清算交收程序的合同,法律似應規定破產管理人不得行使撤銷權,以維護清算交收系統的交收最終性。
注釋:
[1]高富平主持.證券登記結算數據電子化的法律問題研究[R].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證券登記結算重大法律課題研究報告[C].97,105.
[2]王靜.電子證券的基本法律問題[A].2008《物權法》與證券市場投資者權益保護高層論壇論文集[C].115.
[3]高富平主持.證券登記結算數據電子化的法律問題研究[R].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證券登記結算重大法律課題研究報告[C].97,105.
[4]董安生主持.證券持有模式及不同持有模式下持有人權利研究[R].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證券登記結算重大法律課題研究報告[C].56.
[5]毛國權主持.證券交易結算擔保體系法律問題研究[R].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證券登記結算重大法律課題研究報告[C].311,297.
[6]毛國權主持.證券交易結算擔保體系法律問題研究[R].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證券登記結算重大法律課題研究報告[C].311,297.
第3篇
內容提要:文章從唐代法律體系和民事契約文書中,概括并揭示出制度與事實上的唐代民事主體、客體和民事法源的基本面貌及其構造。認為唐代民事主體是一不同類別的多層次結構,這—結構是相對開放的等級社會在民事法上的投影。民事客體由物、人(奴婢)和行為三類組成。民事法源由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構成,并以禮(理)為指導,各種法源因此具有相通一致之處。
一
唐代法律向來是傳統中國法的研究重心,可謂成就斐然,惟不稱人意的是唐代民事法素來是研究中的薄弱環節。近年國內出版的幾部中國民事法通史的著作[1]對此有所填補,但涉及民事主體、客體與民事法源的這一部分過于簡略,未能從復雜的唐代法律體系和民事生活中概括和揭示出制度與事實上的民事主體、客體與民事法源的基本面貌及其構造。多年前臺灣潘維和先生的《中國民事法史》[2]也存在這一缺憾。筆者因整理唐代經濟民事法律的原因,重點探討了這個問題,現將初步成果提供給大家批評。
民事主體是指參與民事法律活動,享受權利、承擔義務的人。構成現代民事主體的一般是自然人、法人和合伙。唐代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法人和合伙組織,但有一些相關的特殊組織,至于民事法上的自然人早已有之。基于唐朝是等級社會這一事實,其民事主體可依類別和社會分層簡述如下。
皇帝是傳統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和代表者,作為自然人,他是特殊的民事主體。無論是在身份、物權,還是婚姻、家庭、繼承上,皇不同于一般的主體,享有各種特權。《唐律疏議·名例》稱皇帝是“奉上天之寶命,……作兆庶之父母。”[3]從法理上看,唐代皇帝亦承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4]的傳統,名義上是國家土地的所有人。
國家是現代法律概念,但在唐代可與皇帝、社稷、王朝、江山以至天下相通,這是政治專制主義和文化天下主義的反映。[5]若細作民事法上的分辨,國家與皇帝自有不同。國家不是自然人,不可能象皇帝那樣參與有關身份、婚姻、家庭、繼承諸方面的民事法律活動,但國家可以朝廷和官府的名義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多類財物,包括土地、水源、森林、礦藏、文物和其他無主財產。例如,唐代的公廨田、墾地、官舍等法律上都歸國家所有。同時,國家實際上也以主體身份參與國際民事活動,我們在唐代對外貿易的法律調整中所討論到的“互市”和“市舶”即屬此類。[6]
貴族與官僚是繼皇帝之后的又一類特殊民事主體。依唐令的規定,貴族與官僚可依爵位和官品上下分等。[7]所有貴族、官僚依律可享有“議”、“請”、“減”、“贖”、“當”、“免”的特權,在衣、食、住、行、婚、喪、祭以及繼承等民事行為上,貴族與官僚各按其品級享有不同規格的權利,不得僭越,尤其是不許平民僭越。[8]在最重要的物質資源土地的分配和處分上,貴族與官僚的民事法律特權相對平民極為顯著。[9]
平民在唐律中又稱之為“良色”、“凡人”、“常人”,俗稱“白姓”、“白丁”。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諱,不用“民”字。唐代民分良、賤。平民即是法律上的良民,其主體為廣大的自耕農和中小庶族,獨立的手工業者和商人也是其組成部分。依唐律,平民有獨立的人格,對任何人無人身依附關系,但對國家負有納稅、服役、征防的義務。平民是唐代民事權利的主體,占唐代人口的絕大多數。他們的民事權利在履行法定義務的前提下能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可以自由、獨立地參與各種民事活動,法律嚴禁買賣良人,維護其人格尊嚴。平民中的工商階層較之士農仍受歧視,法律規定種種限制,在農、食、住、行、婚、喪等方面的權利受到抑制,但在稅收和土地分配上卻又重于和少于農民,尤其是“工商之家不得預與士”的規定,剝奪了工商者及其子弟的參政權。[10]這種法律上的“賤商”傳統,至少在制度上維持到清末變法修律前仍無實質性的變化。
賤民是唐代社會分層中最復雜的一個系統,總體上不能視為獨立的民事主體,但又呈現出不同的形態,有的接近良民,有的只是民事權利的客體,還有處于兩者之間的過渡狀態。依唐代律令和習慣,賤民分為官、私兩種。官賤民有官奴婢、官戶(番戶)、工樂戶、雜戶、太常音聲人,[11]私賤民有私奴婢和部曲(包括部曲妻、客女、隨身)。[12]在賤民中,奴婢的地位最低,唐律視同“畜產”,[13]是民事權利的客體。其余官賤民依次由權利客體向權利主體遞進,其中雜戶、太常音聲人地位最高,“受田、進丁、老免與百姓同。其有反、逆及應緣坐,亦與百姓無別。”[14]私賤民中的部曲(妻、客女、隨身)雖與奴婢同為家仆,對其主人有人身依附關系,[15]但部曲不同資財,可與良人通婚,[16]這是奴婢所不能的。然而,良人之女若嫁與部曲為部曲妻,也成賤民。
唐代賤民身份并非固定不變,可通過官方減免、主人放良或自贖免賤實現身份解放。《舊唐書·食貨志》載,官奴婢“一免為番戶(官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并且,隨著社會進步,官戶、官奴婢有廢疾及年逾七十者,都可解除賤民身份。[17]主人放良是私賤民身份解放的重要途徑,唐朝有令:“諸放部曲客女奴婢為良及部曲客女者,并聽之,皆由家長給手書,長子以下連署,仍經本屬申牒除附。”[18]放良雖是私人行為,但法律還是予以必要規范,放良后還壓者,唐律視為犯罪,規定:“若放部曲、客女為良,壓為賤者,徒二年。……放部曲、客女為良,還壓為部曲、客女,及放奴婢為良,還壓為賤,各減一等,各徒一年半。……放奴婢為良,壓為部曲、客女,……又各減一等合徒一年。仍并改正,從其本色。”[19]唐代民間有放良習慣,并有“樣文”提供,其格式類于其他債券,精神合于唐令要求,較為典型的一件是下列“九世紀敦煌放良文書格式”:[20]從良書奴某甲、婢某甲,男女幾人。吾聞從良放人,福山峭峻;壓良為賤,地獄深怨(淵)。奴某等身為賤隸,久服勤勞;旦起肅恭,夜無安處。吾亦長興嘆息,克念在心。饗告先靈,放從良族。枯鱗見海,必遂騰波;臥柳逢春,超然再起。任從所適,再不該論。后輩子孫,亦無闌.官有(政)法,人從私斷。若違此書,任呈官府。
年月日郎父兒弟子孫
親保親見村鄰長老官人官人
主人放良,原因不一。由上述“放良書”可知,主要是被放的奴婢“久服勤勞”感動了主人。雖然這是“樣文”,但應是現實生活的提煉。依律令規定,私奴婢自贖也可以免賤,所謂“自贖免賤,本主不留為部曲者,任其所樂。”[21]賤民與良民是兩種身份等級,在刑事、行政、民事權利上都有巨大的差別。刑事上賤犯良重于良犯賤;行政上賤民子弟不入科舉仕途;民事上賤民沒有獨立的戶籍,奴婢和接近奴婢的官戶、工樂戶視同財產,他們的財產權、交易權均不完整、獨立,也不能與良人通婚,只能“當色為婚”。[22]賤民從良后,身份獲得解放,各項權利與良民同,并享有免除三年賦稅的優待。[23]
唐代還有兩種身份特別的民事主體,按現代習慣可概稱為宗教人士和外國人。唐令:“諸道士女道士、僧尼之簿籍,亦三年一造(其籍一本送祠部,一本送鴻臚,一本留于州縣)”。[24]這條法令透露出這樣的信息,唐代合法的宗教人士是男女道士和男僧女尼。這四種人因在國家登記,享有與其身份相應的民事權利。唐令“諸道士受以上,道士給田三十畝,女官二十畝,僧、尼受具戒準此。”[25]由于身份限制,他們不能過世俗的婚姻家庭生活,有關婚姻家庭方面的權利只有還俗后才能恢復,但一般的物權和債權受到保護,他們或以個人身份或以寺、觀名義占有地產,從事商貿和放債活動,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中這方面的債契并不少見。[26]
唐是一開放的等級社會,聲威遠揚,入唐經商、求學、傳經、進俸、旅游以及官方的貢使等外國人數目驚人。唐在華夷有別的觀念支配下,概稱外國人為夷或胡,但唐初基于開放的政策和風氣,對在唐的外國人仍予較高的待遇。外國人可以娶唐人為妻,但不能攜帶回國。胡商可以在中國置產業、開宅第、經商、放貸,各項民事活動多受唐律保護。[27]
概括唐代的民事主體,可獲得這樣簡單的認識:其在大的類別上有自然人與非自然人(國家或官府)、中國人與外國人之分;中國人又有僧、俗兩界;俗界中的皇帝(皇室)、貴族、官僚是享有特權的民事主體,良民雖是主體,但士農與工商又有差別;至于賤民,即如前述,從準權利主體遞減至權利客體。這樣看來,唐代的民事主體是一不同類別的多層次結構。這一結構可以說是相對開放的等級社會在民事法上的投影。
民事主體必然享有權利能力。對自然人言,這種能力一般始于出生,終于死亡。包括唐律在內的傳統中國法律對這種能力雖沒有明確、統一的規定,但應理所當然,只是法律和禮基于等差,如華夷、君臣、士庶、男女、良賤、尊卑、長幼、嫡庶的差別,其權利能力并非平等。如家族之內,子女卑幼法理上雖是民事主體,但其財產權大受限制。唐律有規定:“諸同居卑幼,私輒用財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疏議曰:“凡是同居之內,必有尊長。尊長既在,子孫無所自專。若卑幼不由尊長,私輒用當家財物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28]民法上的權利能力實際含有義務方面,稱為義務能力。但同樣有趣的是,依傳統中國法律,不獨權利能力受限,義務能力也欠完整。唐律:“諸嫁娶違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獨坐主婚。”[29]之所以“獨坐主婚”,乃是因為男女婚姻,本非自由,既無權利,也無義務,所以非法結婚者,男女當事人不負法律上的責任。按法理,婚姻當事人應負有責任,但家族主義已限制了當事人的這項義務能力。
有效的民事行為要求當事人在擁有權利能力之外,還需有行為能力。權利能力是享有權利之資格,行為能力為實行權利之資格。所以權利能力重在享有,行為能力重在行使。要正確地行使這種能力,權利主體必須具備成熟的理智,能認識到自己行為的意義。現代民法一般以年齡作為確定行為能力的依據,通常所說的“成年”即是理智成熟的標志。傳統中國法律上的成年謂之“成丁”,成丁之制歷代皆有。唐初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定令:“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歲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30]大寶三年(公元744年)制:“百姓以十八以上為中,二十三歲以上成丁。”[31]廣德元年(公元763年)又制:“百姓二十五歲成丁,五十五為老。”[32]由此觀之,唐代的成丁年齡大凡三變,高祖時以21歲為成丁,玄宗時改23,代宗時又增至25.這是法律上的一般規定,實際丁年有所不同。唐前期推行均田制,丁歲受田亦即法律認定2l歲具有獨立從事農桑、承擔國家賦稅的能力,但唐律令同時又規定:“諸給田之制有差,丁男、中男以一頃(中男年十八已上者,亦依丁男給)。”[33]又《唐律疏議·戶婚》“嫁娶違律”條略云:“其男女被逼,若男年十八以下及在室之女,亦主婚獨坐。”表明唐律令實際視男子18歲為成丁之年,所以18歲中男與丁男同樣受田,18歲以下被逼成婚可不承擔責任。我國現行民法也以18周歲作為自然人取得完全行為能力的年齡標準,[34]由此可見基于經驗而確立的唐代實際丁年之制所具有的科學性。
二
我們在依次闡釋了唐代民事主體的分類及其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后,還有必要對與此相關的權利客體略作說明。在民事法律關系中,權利客體是民事權利和民事義務共同指向的對象。從實際生活出發,唐代民事權利客體,可以粗分為物、人(奴婢)和行為三類。傳統中國的法律中沒有現代民法上“物”的概念,也沒有“動產”與“不動產”的明顯差別,但都稱有其意。傳統中國法和習慣通常稱動產為物、財或財物,不動產為產、業或產業。動產屬于私人時,稱為私財或私物;屬于國家時,稱為官財或官物。綜稱動產與不動產時,通用財產,有時也用“物”之字樣。唐律上的動產種類繁多,包括錢財、雜物、衣飾、畜產和奴婢之類(奴婢特殊,容后再議)。唐律上的不動產有土地及其附著物。土地依其主體不同,別有王田、官田、寺田、廟田、祭田、私田等;又因其用途、種類不同,而有各種名稱,如園地、基地、墓地、山場、鹽灘、牧地、陂塘、獵場等。土地上的附著物有兩種情況,一是附著于土地而為從物,如草木果實、工作物及礦物等;—是獨立為不動產物權的標的物,如房屋(宅)、邸店、碾硙等。[35]
唐律對物一般都加以保護,但山野無主之物需經人工處理才視為財產。一旦視為財產,即受法律保護。唐律規定:“諸山野之物,已加功力刈伐積聚而輒取者,各以盜論。”疏議曰:“‘山野之物’,謂草、木、約、石之類,有人已加功力,或刈伐,或積聚,而輒取者,‘各以盜論’,謂各準積聚之處時價,計贓,依盜法科罪。”[36]
唐代對物的占有和流通有特別的規定。《唐律疏議·名例》“犯禁之物”條疏議曰:“甲弩、矛矟、旌旗、幡幟及禁書、寶印之類,私家不應有者。”這些物品禁止私人擁有。同時,唐前期一般禁止買賣永業田與口分田,除非特殊情況,[37]這部分土地一般不能成為債權的標的物。唐后期均田制瓦解,土地移轉事實上不受限制,土地的租佃、買賣成為普遍現象。
奴婢是唐代特殊的民事權利客體,任由主人支配,其法律根據即是唐律視他們為畜產之類的物。依律,主人對其奴婢可以占有、使用、買賣、抵押、贈送、放良等。唐律嚴禁買賣奴婢以外的其他人特別是良民或以他們質債,[38]但實際是禁而不止,釀成民間的一種非法習慣。
與物和奴婢不同,行為是民事權利的普通客體。作為權利客體的行為是指權利人行使權利和義務人履行義務的活動。行為主要是債權關系的客體,有“給”、“做”、“提供”三種形式,涉及的契約類型分別有買賣、承攬、運送和保管等。這些類型的債契廣泛存在于有唐一代,張傳璽教授主編的《中國歷代契約匯編考釋》上冊一書中收有多件此類契約文書,閱者可以參見。[39]
三
民事法源是民事法律淵源的簡稱,也即人們所謂的民事法律表現形式,是指導、規范民事活動,處理民事糾紛的法律依據。現代民事法律淵源有成文法與不成文法[40]或兩者的混合三種模式,一般都比較明確。傳統中國由于沒有獨立的民法典,在法律體系和結構上又不同于西方,所以沒有現代意義上統—的民事法律淵源,唐代亦不例外,但事實上存在著不同的民事法源并形成一定的結構。
整體看,唐代民事法源應是成文法與不成文法相混合的模式。在成文法方面有完整的律、令、格、式和相類似的制、詔、敕等各種命令,這些命令統稱為敕令。唐代“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范立制,格以禁違止邪,式以軌物程事。”[41]凡治國必遵循令、格、式所確定的制度和規范,違者,一斷以律。[42]唐“律”在不同時期有所增損,但可以《唐律疏議》為代表。《唐律疏議》十二篇,其中與民事行為聯系較為緊密的有《名例》、《戶婚》、《廄庫》、《斗訟》、《雜律》、《斷獄》諸篇。唐令是成文法中正面規定民事活動規則的主要法律形式,內容廣泛、數量龐大。從仁井田升整理的《唐令拾遺》內容看,涉及民事法律較多的有《戶令》、《封爵令》、《衣服令》、《儀制令》、《田令》、《賦役令》、《關市令》、《喪葬令》、《雜令》等。格、式由于散失,難以判別其與民事法律的相關內容,只能從《宋刑統》所引的唐代法令中窺見格、式也有關于民事的規定。[43]律、令、格、式均制定并完備于唐前期,[44]隨著社會變化,特別是到唐后期,很多規定漸成具文,被源于皇權的敕令取而代之。這些敕令經整理匯編后稱為“格后敕”,成為民事領域重要的成文法淵源。
成文法是唐代民事法律的重要法源,但不是全部,民事實踐中長期并存著多種同樣重要的法源。這些法源與成文法相對應并起著補充作用,可統稱為不成文法。依目前的梳理,唐代民事法源中的不成文法主要有習慣、禮和法理。“習慣”包括—般的慣例、習俗(鄉法)和樣文。慣例是民間約定俗成的一種民事規范,國家成文法對之并不加以限制。唐令規定某些民事行為“任依私契,官不為理。”[45]在唐代多種契約文書中,常見有“官有政法,人從私契”的慣語。當時契約的種類、形式、內容等也主要依據民間慣例,表明慣例在唐代民事債權領域中有廣泛的適用。[46]習俗是一種鄉村風俗,唐律又稱“鄉法”。《唐律疏議·雜律》“非時燒田野”條疏議曰:“諸失火及非時燒田野者,笞五十。(非時,謂二月一日以后,十月二十三日以前。若鄉土異宜者,依鄉法。)議曰:謂北地旱早,南土晚寒,風土亦既異宜,各須收獲終了,放火時節不可一準令文,故云‘各依鄉法’。”此處“鄉法”非特指民事,但它是國家司法的依據,對民事行為和民事糾紛的處理自然有指導作用。《唐律疏議》中明確提及鄉法的尚有若干處。[47]還有一種與慣例和鄉法相聯系的“樣文”在唐代出現。樣文實質是對慣例和鄉法的總結、提煉,是民事關系復雜后慣例和鄉法的格式化,對民間多種民事行為具有直接、高效的指導和規范作用。從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中發現有分家、放良、放妻、遺囑多件樣文格式。[48]實際唐代其他種類的契約文書格式化同樣顯著,譬如成立契約的“和同”要件、擔保條款、附署人名、畫指為信等如出一轍。[49]
“禮”是傳統中國最重要的法律淵源,在民事領域有廣泛深遠的影響,以致有論者提出禮即是傳統中國的民法。[50]禮源于華夏先民的日常生活和原始宗教經驗,最初內容無所不包,但其內在精神是依據血緣和等級,區分人們的上下、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并以此決定各自權利義務的差別。[51]禮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遷,到唐朝,禮在法律及其民事法方面的突出表現,首先是禮的法律化。唐代立法貫徹“禮法合一”的原則,把禮的規范法律化,賦予禮的“尊尊”、“親親”以法律關系的性質,從而使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統一起來,[52]所謂“失禮之禁,著在刑書。”[53]唐代有關身份、物權、債權、婚姻、家庭、繼承較穩定的民事法律原則都是這種“禮法合一”的產物。從法律淵源角度說,這部分內容正是成文法的范疇,這里提出來,是想指出它們在淵源和性質上不脫禮的樊籠。
禮在唐代民事法源上的不成文法形式主要有禮教和禮俗。禮教是對禮之精神的抽象、闡釋和改造,屬于道德范疇,是傳統中國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也是社會大眾的主流文化價值觀。它的“綱常名教”深入人心,在影響國家民事立法、司法的同時,還十分有力地指導、規范、調整民間的民事行為和民事關系。《唐律疏議·職制》“匿父母及夫喪”條疏議:“問曰:”居期喪作樂及遣人作樂,律條無文,合得何罪?‘答曰:《禮》云:“大功將至,辟琴瑟。’……況乎身服期功,心忘寧戚,或遣人作樂,或自奏管弦,須加懲戒。律雖無文,不合無罪。從‘不應為’之坐:期喪從重,杖八十。”這條涉及到特殊時期(喪期)家庭身份倫理的規范,在“律條無文”的情況下,援禮為據,杖八十,典型反映了不成文法的禮教對成文法淵源的補充。這種情形在唐“律”的“疏”和“議”中相當常見。禮教作為習慣法淵源的一種形式是官方對禮教經典的整理匯編,如《十三經注疏》、《大唐開元禮》等。這些經典借助官方的作用,強化了人們的禮教觀,成為重要的民事法源,在婚姻、家庭和民事訴訟中有直接影響。禮在發展過程中還有—部分逐漸與法律分離,演變成習俗性的禮俗,如民間婚姻禮俗千姿百態,其與“六禮”相悖者,皆不受制裁。禮俗的范圍十分廣泛,是民間民事生活中事實上的法源。[54]
唐代民事法源還有很重要的—項是“法理”。法理是在沒有直接現成的成文法(律、令、格、式正條與敕令)和習慣、禮教、禮俗的情況下,司法機關或當事人依據相近的法律、判例、事理或禮,就某項民事行為或爭議所做出的合乎法律精神和原理的推理、解釋。此推理、解釋填補了法律依據上的空白,構成新的法源。唐律雖無“法理”之名詞,但有名異實同的“比附”和“事理”之規定。比附是一種類推性的法律解釋,通常有兩種,一是以律相比,一是以例相比。以律相比,《唐律疏議》規定:“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55]所謂出罪,就是要減輕或免除處罰時,可以舉重罪比照輕罪,以明確對輕罪的處理。《疏議》舉例說,夜間無故闖入人家者,主人頓時殺之,律不為罪。如果主人有折傷行為,對此類行為律雖無規定,但比殺死為輕,自然也就不負責任。所謂入罪,就是決定處罰和加重處罰時,可以舉輕罪比照重罪,明確對重罪的處理。如《疏議》規定,凡預謀殺死期親尊長者,皆斬。如果已殺傷,比預謀重,因此,殺傷雖無正條,但比照預謀,應處死刑。這種輕、重相舉的比附實質是一種司法推理的過程。以例相比,就是法無明文規定時,可以參照成例如《法例》,解釋例如《唐律疏議》中的“疏”、“議”、“注”等,[56]通過比照解釋,構成新的法律依據。
關于典型的法理解釋,唐律有一規定:“諸不應得為而為之者,笞四十(謂律令無條,理不可為者);事理重者,杖八十。”[57]律文中的“不應得為”、“理”、“事理”,在唐代都是與“禮”相通的—種法理,[58]推究起來就是法理解釋。如《唐律疏議·戶婚》“有妻更娶”條:“問曰:有婦而更娶妻,后娶者雖合離異,未離之間,其夫內外親戚相犯,得同妻法以否?答曰:一夫一婦,不刊之制,有妻更娶,本不成妻。詳求理法,止同凡人之坐。”回答表明唐律雖無一夫一妻的明文規定,但這是不刊之制,因此,有婦之夫娶的第二婦人不能視為妻子,離異前其夫內外親戚相犯,不依“親戚相犯”條而依“凡人”相犯條處理。理由是依據不刊之制的“理法”,第二婦人不具有妻子的身份,相犯者自然也就不能享有因夫妻身份而產生的權利。這是通過身份的認定,經由民事主體而決定刑事責任的法理解釋。在傳統中國的司法文書和契約文書中時見有“理”、“情理”、“天理”之類的詞語,[59]表明現代所謂的“法理(解釋)”自是中國民事法上固有的法源。
從法源構造的角度來概括上述認識,我們可以發現,唐代民事法律淵源已形成一定的結構。律、令、格、式是“天下通規”,[60]所以,唐律規定:“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61]與律、令、格、式相類似的敕令以及經整理匯編而成的“格后敕”形式上是補“正文”之不足的特別法,實際效力卻與“天下通規”無異,唐后期更是優于律、令、格、式。[62]藉此,筆者以為,由律、令、格、式和敕令構成的成文法應是唐代基本的民事法源;相對言,由習慣、禮、法理構成的不成文法則是基本法源的補充。這“補充”有三層含義:一是在法律效力的位階上,基本法源優于補充性法源;二是在基本法源與補充性法源沖突的情況下,補充性法源讓位于基本法源;三是在基本法源空缺的前提下,補充性法源成為替補。唐代民事法源的構造大致不脫此框架,但有兩點需要指出,首先是由于官方對民事總體上持相對消極放任的態度,造成制定法的有關規定過于原則,尤其是民事中的物權、債權領域缺乏系統的明晰規定,形成很多法律缺漏和空白;再是唐代民事成文法上的原則性規定不能涵蓋新出現的、特殊的民事法律關系,這些因素必然給不成文法的調整留下相當寬裕的空間。這樣,不僅成文法為不成文法所彌補成為必然,而且不成文法在數量和適用空間上也有可能超出成文法。需要指出另一點是,在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的內部也有一定的結構。簡單說,成文法方面,唐前期凡涉及民事且法律又有規定的,官方、民間都依“令、格、式”處理,若有糾紛一斷以“律”。唐后期“敕令”和“格后敕”,在物權、債權、繼承等領域優先適用;身份、婚姻、家庭領域,律、令、格、式則繼續有效。不成文法方面,有關物權尤其是債權的一般民事行為適用“習慣”的空間很大;涉及身份、婚姻、家庭的民事方面“禮”有優勢;民事行為轉為民事訴訟后,法無明文規定者,“法理”顯得特別重要,習慣和禮能否替代或破法理還是問題。當然,法理本身與習慣和禮能夠溝通,它們本質上都不脫一個“禮(理)”字。這是唐代民事法律淵源構造的精神紐帶,也即在“禮法合一”的前提下,成文法與不成文法皆以禮(理)為指導,各種法源具有相通一致之處。
注釋:
﹡張中秋,法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1]值得提出的有北京大學李志敏教授的《中國古代民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復旦大學葉孝信教授主編的《中國民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煙臺大學孔慶明教授等編著的《中國民法史》(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國政法大學張晉藩教授主編的《中國民法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潘維和著:《中國民事法史》,臺北:臺灣漢林出版社1982年版。
[3]《唐律疏議·名例》“謀反”條疏議。
[4]《詩經·小雅·北山》。
[5]參見張晉藩、王超著:《中國政治制度史》,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89-416頁有關唐代皇帝制度的詳細說明;[美]費正清著:《費正清集》(陶文釗選編,林海等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1992年版,第3-26頁有關文化主義的天下秩序觀的論述。
[6]參見張中秋著:《法律與經濟:傳統中國經濟的法律分析》,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頁及以下。
[7]詳見[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遺》(粟勁等譯),長春:長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1頁及以下之“官品令”、“選舉令”、“封爵令”、“祿令”.
[8]詳見《唐律疏議·名例》“議章”、“請章”、“減章”、“贖章”、“官當”、“除名”、“免官”、“免所居官”,及《唐令拾遺》之“衣服令”、“鹵薄令”、“假寧令”、“喪葬令”等。
[9]見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遺》第539頁及以下之“田令”。
[10]見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遺》第206頁;《唐律疏議·詐偽》“詐假官假與人官”條疏議。
[11]官奴婢是因罪沒官的家人及其后代。官戶(番戶)隸屬于中央朝廷的司農寺。工樂戶隸屬于中央朝廷的少府和太常寺。雜戶隸屬于州縣。太常音聲人原屬太常寺,唐初改隸州縣。雜戶和太常音聲人地位稍高,接近良人,其余接近奴婢。
[12]私奴婢來自奴婢的后代或市場買得。部曲在南北朝時原是私人武裝,唐時轉為家仆。《唐律疏議·名例》疏曰:“部曲,謂私家所有”。同時,《唐律疏議·賊盜》疏又云:“部曲不同資財”,說明部曲比奴婢地位略高,是一種對主人有人身依附關系的賤民。部曲妻、客女和隨身都是私主的家仆。
[13]《唐律疏議·名例》“官戶、部曲、官私奴婢有犯”條:“奴婢,律比畜產。”
[14]《唐律疏議·賊盜》“緣坐非同居”條疏議。
[15]《唐律疏議·斗訟》“主毆部曲死”條疏議:“部曲、奴婢,是為家仆”。
[16]《唐律疏漢·戶婚》“部曲,謂私家所有,其妻通娶良人、客女、奴婢為之。”
[17]《唐會要》卷八六《奴婢》:“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十月敕:當司應管諸司,所有官戶、奴婢等,據《要典》及令文,有‘免賤從良’條。近年雖赦敕,諸司皆不為論,致有終身不沾恩澤。今請諸司諸使,各勘官戶奴婢,有廢疾及年近七十者,請準各令處分。”
[18]見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遺》第170頁。
[19]《唐律疏議·戶婚》:“放部曲為良還壓”條疏議。
[20]轉引自張傳璽主編:《中國歷代契約匯編考釋》(上),北京:北京大學山版社1995年版,第480頁。
[21]見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遺》第170頁。
[22]詳見《唐律疏議·戶婚》“奴娶良人為妻”條疏,“雜戶客戶與良人為婚”條疏。
[23]《文獻通考·職役考二·復除》:“唐制:……奴婢縱為良人,給復三年。”
[24]見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遺》第795頁。
[25]見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遺》第568頁。
[26]見前注揭張傳璽主編《中國歷代契約匯編》(上)第213、220-221、318頁。
[27]參見[美]謝弗著:《唐代的外來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2頁;高樹異:“唐宋時期外國人在中國的法律地位”,載《吉林大學學報》,1978年第5-6期。
[28]《唐律疏議·戶婚》“同居卑幼私輒用財”條。
[29]《唐律疏議·戶婚》“嫁娶違律”條。
[30]《舊唐書·食貨記》。
[31]《通典·食貨·丁中》。
[32]《通典·食貨·丁中》。
[33]見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遺》第542頁。
[34]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1條之規定。
[35]以上參考前注揭潘維和著《中國民事法史》第216頁及以下。
[36]《唐律疏議·賊盜》“山野之物已加功力輒取”條。
[37]“諸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即流移者亦如之。樂遷就寬鄉者,并聽賣口分(賣充住宅、邸店、碾硙者,雖非樂遷,亦聽私賣)。”(見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遺》第560頁)
[38]見《唐律疏議·雜律》“以良人為奴婢質債”條。
[39]詳見前注揭張傳璽主編《中國歷代契約匯編》(上)“唐代契約”部分。
[40]成文法與不成文法并不能簡單以有無文字表現為區別。學理上視成文法為由國家機關制定和公布并以法律條文形式出現的法,又稱制定法。不成文法是指國家機關認可其具有法律效力而不具有條文形式的法律,可以有文字表現如判例法,也可以無文字表現如習慣。因不成文法淵源于習慣,所以又稱習慣法。
[41]《唐六典》卷六。
[42]《新唐書·刑法志》。
[43]詳見《宋刑統·戶婚》引唐敕令等。
[44]詳見張晉藩總主編、陳鵬生主編:《中國法制通史·隋唐》,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46頁。
[45]見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遺》第789頁。
[46]詳見前注揭張傳璽主編《中國歷代契約匯編》(上)有關唐代契約的部分。
[47]參見《唐律疏議》卷十三、卷十九。
[48]參見前注揭張傳璽主編《中國歷代契約匯編》(上)第454~506頁。
[49]參見前注揭葉孝信主編《中國民法史》第260-263頁。
[50]見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遺》第52-54頁。
[51]《管子·五輔》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別、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
[52]詳見張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頁及以下;劉俊文:“唐律與禮的密切關系例述”,載《北京大學學報》,1984年第5期。
[53]參見《全唐文·薄葬詔》。
[54]詳見文史知識編輯部編:《古代禮制風俗漫淡》(一集、二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1986年版。
[55]《唐律疏議·名例》“斷罪無正條”條。
[56]依新舊唐書《刑法志》記載,唐前期曾將判例整理匯編成《法例》,供司法實踐參照。又,潘維和先生認為,《唐律疏議》之“疏”、“議”、“注”即是一種解釋例。(見前注揭潘維和著《中國民事法史》第16頁)
[57]《庸律疏議·雜律》“不應得為”條。
[58]《禮記·仲尼燕居》“禮也者,理也。
[59]詳見《名公書判清明集》,卷四-卷十,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
[60]《舊唐書·刑法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