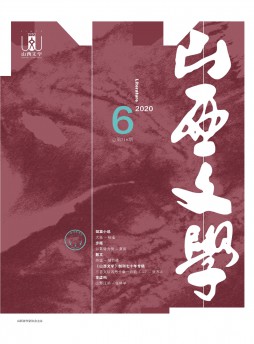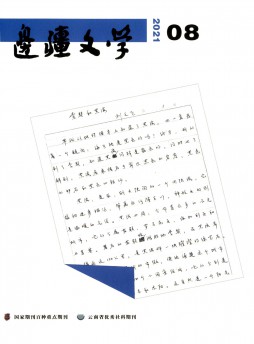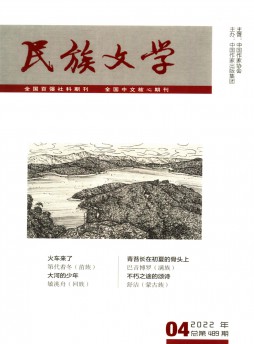文學(xué)批評(píng)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shù)篇優(yōu)質(zhì)文學(xué)批評(píng)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lái)啟發(fā),助您在寫(xiě)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新批評(píng)”作為最先進(jìn)的西方文論之一傳入中國(guó),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píng)影響最大的莫過(guò)于語(yǔ)言意識(shí)的轉(zhuǎn)變。瑞恰慈在他的文學(xué)批評(píng)思想中,對(duì)語(yǔ)言與思想的關(guān)系進(jìn)行了討論,對(duì)文學(xué)語(yǔ)言與科學(xué)語(yǔ)言進(jìn)行了劃分。他認(rèn)為,思想與語(yǔ)言之間是直接的因果關(guān)系,思想是因,語(yǔ)言是果,語(yǔ)言是表達(dá)思想的符號(hào)。而語(yǔ)言又可分為文學(xué)語(yǔ)言與科學(xué)語(yǔ)言,文學(xué)語(yǔ)言是用以喚起某種情感的,是情感語(yǔ)言;科學(xué)語(yǔ)言是用以指稱(chēng)某個(gè)對(duì)象的,是符號(hào)語(yǔ)言。瑞恰慈的語(yǔ)言觀使中國(guó)學(xué)者意識(shí)到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學(xué)批評(píng)對(duì)語(yǔ)言意識(shí)認(rèn)識(shí)的輕慢。中國(guó)古代文論早有言意之辯,文學(xué)語(yǔ)言是文學(xué)的載體還是本體成為言意之辯的核心話題。中國(guó)傳統(tǒng)載體論語(yǔ)言觀認(rèn)為,語(yǔ)言是文學(xué)的載體,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和思維工具,是外在的媒介,本身沒(méi)有獨(dú)立價(jià)值。古典詩(shī)學(xué)的儒道佛三家,雖信奉的本體論各異,語(yǔ)言觀卻驚人地一致,他們都認(rèn)為語(yǔ)言只是文學(xué)的載體。儒家的“詩(shī)言志”、孔子的“辭達(dá)”說(shuō),都認(rèn)為文學(xué)語(yǔ)言是言志、載道的工具,是文學(xué)的載體。莊子也提出,載意之言與捉兔之網(wǎng)、捕魚(yú)之笱性質(zhì)相同,作用一致,語(yǔ)言無(wú)非是獲取意義的手段和工具,意義才是目的。一旦獲取意義,達(dá)到目的,作為工具的語(yǔ)言便毫無(wú)用處,可以被忘卻,這就是所謂的“得意而忘言”。佛家禪宗的布道方式是“拈花微笑”“當(dāng)頭棒喝”,其要旨是避免拘執(zhí)于語(yǔ)言而迷失本源,因此只有廢棄語(yǔ)言才能悟道。這種對(duì)言意關(guān)系的認(rèn)知深刻地影響了幾千年來(lái)中國(guó)文學(xué)批評(píng)的語(yǔ)言意識(shí),在文學(xué)批評(píng)中,載體論的語(yǔ)言觀是反映論和表現(xiàn)論的基礎(chǔ)。反映論認(rèn)為,文學(xué)語(yǔ)言是反映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工具。表現(xiàn)論認(rèn)為,文學(xué)語(yǔ)言是表現(xiàn)作家和人物內(nèi)心的載體,語(yǔ)言一旦完成了反映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和表現(xiàn)人物內(nèi)心的任務(wù),就可以被遺忘了。這種批評(píng)方式一直是中國(guó)文學(xué)批評(píng)的主流,由于長(zhǎng)期以來(lái)人們只關(guān)注語(yǔ)言的載體性能,而沒(méi)有認(rèn)識(shí)到文學(xué)語(yǔ)言本身的價(jià)值,中國(guó)文學(xué)批評(píng)的主要任務(wù)便是在語(yǔ)言的背后去尋找文學(xué)作品的“歷史意義”“現(xiàn)實(shí)意義”和“審美特性”了。中國(guó)傳統(tǒng)文論中語(yǔ)言意識(shí)的薄弱,給中西文化交流帶來(lái)重重阻礙,也使得人們的思想交鋒陷入困境。“西學(xué)東漸”之前的中國(guó)文論多是思想意識(shí)的辯論,而較少關(guān)注于語(yǔ)言意識(shí)的準(zhǔn)確表達(dá)。“新批評(píng)”的引入,促使中國(guó)學(xué)者重新思考思想與語(yǔ)言的關(guān)系,更為重視語(yǔ)言在文學(xué)中的重要作用,李安宅便是其中之一。在瑞恰慈的影響下,李安宅開(kāi)始關(guān)注語(yǔ)言與思想的關(guān)系,深入探索文學(xué)語(yǔ)言的意義,開(kāi)始實(shí)現(xiàn)了語(yǔ)言意識(shí)的最初自覺(jué)。他在《意義學(xué)》一書(shū)中指出:“凡事都是先有自覺(jué),然后才有系統(tǒng)的研究,普遍的進(jìn)步。涌現(xiàn)于現(xiàn)代思潮的有自我意識(shí),社會(huì)意識(shí),種族意識(shí),性的意識(shí)等,正不妨添上一個(gè)‘字的意識(shí)’或‘語(yǔ)言意識(shí)’。”李安宅意識(shí)到了語(yǔ)言意識(shí)長(zhǎng)久的沉默狀態(tài),主張喚起文學(xué)研究的語(yǔ)言意識(shí):“研究語(yǔ)言、分析語(yǔ)言、改良語(yǔ)言,使它成為我們的隨手工具,沒(méi)有人為物役的毛病,是我們的歷史使命。”[2]11由此可見(jiàn),對(duì)于語(yǔ)言意識(shí)的重新認(rèn)識(shí)和呼喚語(yǔ)言的自覺(jué),成了李安宅一代學(xué)者的歷史使命。這種使命感警示了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學(xué)批評(píng)對(duì)語(yǔ)言意識(shí)的輕慢與回避,也進(jìn)一步宣揚(yáng)了語(yǔ)言意識(shí)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píng)建設(shè)的必要性。瑞恰慈也熱情地回應(yīng)了李安宅關(guān)于語(yǔ)言意識(shí)自覺(jué)的呼喚。瑞恰慈在華執(zhí)教期間,體驗(yàn)到了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píng)對(duì)于“科學(xué)”的熱情。但他認(rèn)為,“科學(xué)”的實(shí)質(zhì)不僅僅是技術(shù)的進(jìn)步,更為重要的是采用一種以語(yǔ)言意識(shí)為核心的思維方式,“中國(guó)人需要科學(xué),并不像現(xiàn)在許多人覺(jué)得那樣,以為科學(xué)是什么把戲,實(shí)在因?yàn)榭茖W(xué)是一種思想的途徑”。他認(rèn)識(shí)到,中西語(yǔ)言觀念是存在差異的,“在西洋,則對(duì)于語(yǔ)言作用的見(jiàn)解,不管是公開(kāi)地或是秘密地,都有支配我們底思想的力量,支配了兩千多年”。中國(guó)的情況則相反,“中國(guó)的歷史里面,對(duì)于語(yǔ)言的結(jié)構(gòu)與種類(lèi),不同的字眼所有的種類(lèi)不同的作用,都沒(méi)有發(fā)展成固定的理論”。瑞恰慈指出中西語(yǔ)言觀念的差異源于思想觀念的不同,西方在語(yǔ)言意識(shí)的基礎(chǔ)上建立了科學(xué),科學(xué)精神的完善推動(dòng)了科學(xué)的進(jìn)步,語(yǔ)言意識(shí)是科學(xué)的基礎(chǔ),在此基礎(chǔ)上,中國(guó)必須關(guān)注語(yǔ)言與思想的關(guān)系,關(guān)注語(yǔ)言研究,強(qiáng)化語(yǔ)言意識(shí),才能構(gòu)建現(xiàn)代科學(xué)精神,才能真正地引進(jìn)西方的科學(xué)。“新批評(píng)”的語(yǔ)言觀是西方眾多語(yǔ)言理論中的一種,但是對(duì)于中國(guó)文學(xué)批評(píng)界來(lái)說(shuō),“新批評(píng)”采取理性的態(tài)度考察思想脈絡(luò),研究語(yǔ)言?xún)?nèi)涵,建構(gòu)科學(xué)認(rèn)知方式,這無(wú)疑是喚醒“語(yǔ)言自覺(jué)”的第一聲春雷,也是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學(xué)批評(píng)的一種有益補(bǔ)充。當(dāng)然,“五四”以后中國(guó)文學(xué)批評(píng)的“語(yǔ)言的自覺(jué)”還是比較模糊的,由于“新批評(píng)”與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學(xué)批評(píng)的異質(zhì)性,使得“新批評(píng)”在中國(guó)的傳播與影響受到限制。再加上特殊的政治歷史條件,內(nèi)有國(guó)內(nèi)戰(zhàn)爭(zhēng),外有俄國(guó)十月革命,“五四”時(shí)期對(duì)西方文論的接受由“先進(jìn)”的歐洲文論轉(zhuǎn)向了蘇俄文論,在之后半個(gè)世紀(jì)的時(shí)間內(nèi),蘇俄文論一直在中國(guó)文論中占據(jù)主流地位。可是毋容置疑的是,中國(guó)文學(xué)批評(píng)借鑒“新批評(píng)”所喚起的“語(yǔ)言的自覺(jué)”,推動(dòng)了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學(xué)觀念的轉(zhuǎn)向,是文學(xué)走向自由的必由之路,語(yǔ)言意識(shí)的覺(jué)醒也為文學(xué)回到文學(xué)本身,表現(xiàn)更高的生存意向和更復(fù)雜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可能,這是從語(yǔ)言載體論轉(zhuǎn)向語(yǔ)言本體論的必經(jīng)之途。對(duì)于文學(xué)語(yǔ)言本體的重視也就意味著對(duì)文學(xué)所表達(dá)的意識(shí)形態(tài)和社會(huì)政治內(nèi)容的刻意疏離,這為中國(guó)文學(xué)批評(píng)鋪陳了一條不同于社會(huì)政治歷史傳統(tǒng)的詩(shī)性超越之路。而到了20世紀(jì)80年代,中國(guó)文學(xué)批評(píng)界掀起了“文學(xué)本體論”大討論,這一文學(xué)批評(píng)盛事進(jìn)一步證實(shí)了文學(xué)語(yǔ)言本體論建構(gòu)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二、本體建構(gòu):語(yǔ)言轉(zhuǎn)向條件下文學(xué)本體的倡揚(yáng)
如果說(shuō)“五四”以后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píng)借鑒“新批評(píng)”的語(yǔ)言觀,從而引發(fā)了對(duì)于傳統(tǒng)載體論語(yǔ)言觀的反思,那么20世紀(jì)80年代的“文學(xué)本體論”大討論則實(shí)現(xiàn)了本體論語(yǔ)言觀的建構(gòu)。20世紀(jì)80年代,“新批評(píng)”思想卷土重來(lái),文學(xué)語(yǔ)言形式的研究仍是文學(xué)批評(píng)的焦點(diǎn)。“新批評(píng)”倡導(dǎo)對(duì)文本進(jìn)行語(yǔ)義分析,主張文本細(xì)讀,從而使文學(xué)批評(píng)回到文學(xué)語(yǔ)言形式本身。這一理論的重申大大拓寬了中國(guó)文學(xué)批評(píng)家的理論視野,新時(shí)期的批評(píng)家反思傳統(tǒng)的載體論語(yǔ)言觀,開(kāi)始從本體論的高度定位文學(xué)語(yǔ)言,不僅表現(xiàn)在批評(píng)實(shí)踐上,還表現(xiàn)在具體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實(shí)踐中,從而掀起了“語(yǔ)言本體論”的熱潮。從“新批評(píng)”與中國(guó)文學(xué)批評(píng)本體論語(yǔ)言觀建構(gòu)的關(guān)系來(lái)看,“文學(xué)本體論”的理論來(lái)源于“新批評(píng)”。從20世紀(jì)70年代末開(kāi)始,中國(guó)陸續(xù)地翻譯、介紹“新批評(píng)”的相關(guān)理論和批評(píng)家。到了20世紀(jì)80年代,對(duì)于“新批評(píng)”的翻譯、介紹與研究呈現(xiàn)出系統(tǒng)化、規(guī)模化態(tài)勢(shì),其中楊周翰、趙毅衡等是重要代表。他們撰書(shū)立著和發(fā)表重要論文,介紹和傳播“新批評(píng)”理論。趙毅衡在20世紀(jì)80年代出版了當(dāng)時(shí)國(guó)內(nèi)研究“新批評(píng)”的扛鼎之作《新批評(píng)——一種獨(dú)特的形式主義文論》,對(duì)“新批評(píng)”進(jìn)行了深入的研究。另外,還陸續(xù)出現(xiàn)一批“新批評(píng)”的譯介,如劉象愚翻譯的《文學(xué)理論》、趙毅衡編譯的《“新批評(píng)”文集》等,構(gòu)建了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píng)界“新批評(píng)”的知識(shí)譜系。后來(lái)有評(píng)論家稱(chēng):“英美‘新批評(píng)’派的文學(xué)本體論是我國(guó)文學(xué)理論最近幾年來(lái)出現(xiàn)的文學(xué)本體論的來(lái)源之一,國(guó)內(nèi)的文學(xué)本體論的呼喚者也自覺(jué)地向‘新批評(píng)’派尋覓理論武器。”[4]從此處可以得知,中國(guó)文學(xué)批評(píng)呼喚語(yǔ)言本體論,與“新批評(píng)”的文學(xué)本體論有極大的關(guān)聯(lián)。“新批評(píng)”的價(jià)值,在于為中國(guó)文學(xué)批評(píng)回歸本體提供了理論資源,但是,它不是通過(guò)自身的理論體系來(lái)證明的,而是通過(guò)對(duì)統(tǒng)治中國(guó)已久的反映論的批判來(lái)實(shí)現(xiàn)的。其次,“新批評(píng)”本體論語(yǔ)言觀是對(duì)“反映論”的糾偏,是對(duì)載體論語(yǔ)言觀的顛覆。自“五四”以來(lái),一直統(tǒng)治中國(guó)文學(xué)批評(píng)界的是反映論的文藝觀。“反映論”與“新批評(píng)”的文學(xué)本體論最為抵牾,“文藝觀是反映論的,這被認(rèn)為與新批評(píng)的本體論主張截然對(duì)立”[5]69。在此基礎(chǔ)上,“新批評(píng)”作為一種“清道夫”式的文論,主要的使命是擾亂學(xué)界的既定秩序,以引起人們對(duì)傳統(tǒng)反映論文藝觀的懷疑,對(duì)載體論語(yǔ)言觀的批判。因此,“新批評(píng)”的存在意義是通過(guò)對(duì)“反映論”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的批判,打破文學(xué)批評(píng)界的既定秩序,使人們對(duì)權(quán)威和傳統(tǒng)產(chǎn)生懷疑,為中西文論的融合開(kāi)拓空間。故而,“新批評(píng)”在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píng)界的重要價(jià)值:一方面,憑借“文學(xué)本體論”闡釋文學(xué)語(yǔ)言在文學(xué)中的本體地位;另一方面,通過(guò)批判“反映論”,建立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píng)的新秩序。基于以上兩個(gè)原因,在“新批評(píng)”的影響下,20世紀(jì)80年代后的中國(guó)文學(xué)批評(píng)批判了載體論的語(yǔ)言觀,轉(zhuǎn)而關(guān)注文學(xué)語(yǔ)言自身的價(jià)值和意義,建構(gòu)本體論的語(yǔ)言觀。在進(jìn)行“文學(xué)本體論”大討論時(shí),對(duì)于文學(xué)的本體究竟是什么這個(gè)核心問(wèn)題進(jìn)行了激烈的爭(zhēng)論,大體經(jīng)過(guò)了由“作品本體論”到“語(yǔ)言本體論”的轉(zhuǎn)變。“作品本體論”以作品為核心,其主要理論內(nèi)涵是文學(xué)活動(dòng)以作品為重,文學(xué)批評(píng)應(yīng)面對(duì)作品本身,深入作品內(nèi)部進(jìn)行研究,才可窺見(jiàn)文學(xué)的本質(zhì),文學(xué)研究與作者、世界、讀者等無(wú)關(guān)。持“作品本體論”的批評(píng)家主要有陳曉明、胡經(jīng)之等。“作品本體論”的觀念主要來(lái)自“新批評(píng)”的韋勒克(RenéWellek)。由于受西方現(xiàn)代語(yǔ)言學(xué)派的影響,不難看出“作品本體論”中包含著“語(yǔ)言本體論”的影子。“語(yǔ)言本體論”的一派則以語(yǔ)言為旨?xì)w,高揚(yáng)文學(xué)語(yǔ)言的本體價(jià)值。1985年底,黃子平撰文《得意莫忘言》,提出了須重視文學(xué)語(yǔ)言本身的價(jià)值,“文學(xué)作品以其獨(dú)特的語(yǔ)言結(jié)構(gòu)提醒我們:它自身的價(jià)值。不要到語(yǔ)言的‘后面’去尋找本來(lái)就存在于語(yǔ)言之中的線索。”[6]這既是對(duì)文學(xué)語(yǔ)言的本體意義的強(qiáng)調(diào),也是對(duì)傳統(tǒng)的語(yǔ)言載體論、工具論的有力批判。李劼也在他的《試論文學(xué)形式的本體意味》一文中表達(dá)了相同的思想:“所謂文學(xué),在其本體意義上,首先是文學(xué)語(yǔ)言的創(chuàng)作,然后才可能帶來(lái)其他別的什么。由于文學(xué)語(yǔ)言之于文學(xué)的這種本質(zhì)性,形式結(jié)構(gòu)的構(gòu)成也就具有了本體性的意義。”[7]“語(yǔ)言本體論”將把語(yǔ)言與形式合二為一,形式是內(nèi)容化了的形式,內(nèi)容溶解在形式之中,語(yǔ)言建構(gòu)了文學(xué)的本質(zhì),建構(gòu)了人類(lèi)世界,批判了語(yǔ)言意識(shí)薄弱的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學(xué)批評(píng)。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界,20世紀(jì)80年代的作家們也開(kāi)始秉持本體論的語(yǔ)言觀。語(yǔ)言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不再是反映現(xiàn)實(shí)的工具、承載內(nèi)容的載體。語(yǔ)言就是文學(xué)本身,是文學(xué)的本體,具有獨(dú)立的審美價(jià)值。語(yǔ)言與內(nèi)容相互依存、融為一體,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生命就是語(yǔ)言革新。在“文學(xué)本體論”大討論背景下涌現(xiàn)出的一大批作家表現(xiàn)出了對(duì)于語(yǔ)言形式創(chuàng)新的關(guān)注。劉索拉的《你別無(wú)選擇》、余華的先鋒系列小說(shuō)、于堅(jiān)的詩(shī)歌,都醉心于語(yǔ)言的革新。他們以語(yǔ)言形式的創(chuàng)新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開(kāi)拓了一個(gè)嶄新的空間。作家們不僅在創(chuàng)作實(shí)踐中關(guān)注語(yǔ)言,而且在批評(píng)實(shí)踐上也闡發(fā)了他們對(duì)語(yǔ)言意識(shí)的重視。汪曾祺提出:“中國(guó)作家現(xiàn)在很重視語(yǔ)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識(shí)到語(yǔ)言的重要性。語(yǔ)言不只是一種形式,一種手段,應(yīng)該提到內(nèi)容的高度來(lái)認(rèn)識(shí)語(yǔ)言不是外部的東西。它是和內(nèi)容(思想)同時(shí)存在,不可剝離語(yǔ)言是小說(shuō)的本體,不是附加的,可有可無(wú)的。從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寫(xiě)小說(shuō)就是寫(xiě)語(yǔ)言。”[8]1從汪曾祺的這段話看來(lái),語(yǔ)言于文學(xué)處于顯要的地位,而當(dāng)時(shí)創(chuàng)作界對(duì)語(yǔ)言開(kāi)始充分地重視,其語(yǔ)言觀念也開(kāi)始發(fā)生轉(zhuǎn)變。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文學(xué)批評(píng)界和文學(xué)創(chuàng)作界共同致力于語(yǔ)言意識(shí)的轉(zhuǎn)變,文學(xué)語(yǔ)言觀由語(yǔ)言載體論轉(zhuǎn)向語(yǔ)言本體論,為文學(xué)語(yǔ)言研究的進(jìn)一步深入打下了基礎(chǔ)。“新批評(píng)”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píng)建設(shè)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與其說(shuō)二十世紀(jì)是一個(gè)批評(píng)的時(shí)代,不如說(shuō)二十世紀(jì)是一個(gè)以本體論批評(píng)為主調(diào)的時(shí)代”[9]。而西方各種文論在中國(guó)的“理論旅行”或多或少暗藏著“新批評(píng)”的潛流,“盡管在它之后,西方還涌現(xiàn)了諸如結(jié)構(gòu)主義批評(píng)、原型批評(píng)、后結(jié)構(gòu)主義批評(píng)等等批評(píng)流派,但這些批評(píng)流派在形式本體的意義上基本都是沿著‘新批評(píng)’奠定的研究方向向前發(fā)展”[9]。因而,“文學(xué)本體論”大討論的意義在于,它確立了文學(xué)語(yǔ)言的本體地位,實(shí)現(xiàn)了從語(yǔ)言載體論到語(yǔ)言本體論的轉(zhuǎn)向,改變了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píng)的既有型態(tài),促進(jìn)了文學(xué)語(yǔ)言觀念的全面變化,推動(dòng)了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píng)新的語(yǔ)言范式的建立。但是,20世紀(jì)80年代的“文學(xué)本體論”大討論只是一種理論倡導(dǎo),給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píng)提供了一種文學(xué)研究的新途徑,即從文學(xué)內(nèi)部、文學(xué)形式來(lái)探討文學(xué),卻未建構(gòu)一個(gè)完整的理論系統(tǒng)。無(wú)論是“作品本體論”還是“語(yǔ)言本體論”,都是文學(xué)研究的一種中介,旨在將已被割裂的內(nèi)部研究與外部研究連接起來(lái)。被“新批評(píng)”影響的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píng)在理論重構(gòu)過(guò)程中,遮蔽了“新批評(píng)”自身的理論豐富性,“新批評(píng)”被后世所詬病的“文本”自足性、“文本細(xì)讀”法等也漸漸地與“文學(xué)本體論”大討論之后中國(guó)的理論氛圍格格不入,故而注定了“新批評(píng)”與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píng)只是暫時(shí)的“親密”。更有諷刺意味的是,“文學(xué)本體論”大討論沒(méi)有使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píng)走向“本體論”,而是最終走向了“主體論”。
三、價(jià)值重建:后現(xiàn)代語(yǔ)境下價(jià)值判斷的重建
第2篇
李爾出場(chǎng)的第一句話就是“現(xiàn)在我要向你們說(shuō)明我的心事”。此時(shí)的李爾對(duì)三個(gè)女兒是不加區(qū)分地同等對(duì)待,可是后來(lái)李爾從不加區(qū)分到區(qū)別對(duì)待其實(shí)是劇本設(shè)置的另一結(jié)構(gòu)對(duì)立。這一開(kāi)場(chǎng)承擔(dān)了界定王權(quán)的主要屬性的功能:通過(guò)區(qū)分合格與不合格的繼承人來(lái)控制王國(guó)的繼承權(quán)。合適的繼承人不僅是王室的成員還要具有高貴的品質(zhì),而當(dāng)李爾把阿諛?lè)畛信c高貴的品質(zhì)混為一談時(shí)他也就無(wú)法履行他作為國(guó)王區(qū)分優(yōu)劣繼承人的功能了。這樣從不加區(qū)分到區(qū)別對(duì)待在結(jié)構(gòu)上也就形成了對(duì)立。從法律秩序上來(lái)講,李爾的子女都有機(jī)會(huì)成為繼承人,不應(yīng)該被區(qū)分對(duì)待。而李爾卻很不理智地聽(tīng)信大女兒和二女兒的甜言蜜語(yǔ),放棄了真誠(chéng)的小女兒,李爾的這一感性處理不僅有了對(duì)女兒們的情感偏向,還給自己的王國(guó)帶來(lái)了不可估量的危機(jī)。法律秩序和情感的對(duì)立,即不加區(qū)分到區(qū)別對(duì)待這一結(jié)構(gòu)對(duì)立,也起到了預(yù)示危險(xiǎn)的作用。
二、血緣關(guān)系和高貴品質(zhì)的對(duì)立結(jié)構(gòu)
在一個(gè)以血緣關(guān)系決定繼承的社會(huì)里,如果國(guó)王的繼承人達(dá)不到合法繼承的必要條件,王位的繼承也可以在貴族之間進(jìn)行。這就為第二個(gè)情節(jié)即葛羅斯特情節(jié)作了鋪墊。由于李爾的孩子不能繼承王位,所以必須找到另一個(gè)繼承者。這樣,雙重?cái)⑹陆Y(jié)構(gòu)就在劇中承擔(dān)了一個(gè)重要的敘事功能,即王位的繼承從血緣轉(zhuǎn)到高貴是合理的。于是另一個(gè)結(jié)構(gòu)對(duì)立形成了:在王位繼承問(wèn)題上,李爾的兩個(gè)奸詐的女兒有王室血統(tǒng)卻不高貴,而埃德加高貴卻與國(guó)王沒(méi)有血緣關(guān)系。通過(guò)這樣的對(duì)立,作者巧妙地把王位繼承人從具有血緣關(guān)系的人轉(zhuǎn)到具有高貴品質(zhì)的人上。正如葛羅斯特作為一個(gè)父親和一個(gè)背叛對(duì)象,與李爾是相對(duì)應(yīng)的。而埃德加作為一個(gè)合法的繼承人及不公正的放逐,與考狄利婭的遭遇是對(duì)應(yīng)的。當(dāng)考狄利婭從法國(guó)向英國(guó)進(jìn)軍以恢復(fù)她父親的權(quán)利時(shí),埃德加也潛入敵營(yíng)向埃德蒙挑戰(zhàn)以顯示他具有繼承李爾王位的高貴品質(zhì)。埃德加和埃德蒙的出身也是對(duì)立關(guān)系。而埃德加打敗埃德蒙,既推翻了這個(gè)非法的王位繼承人,又肯定了王位繼承人的標(biāo)準(zhǔn)之一是高貴的品質(zhì),而不是血緣。
第3篇
(一)深厚的家園意識(shí)
朱厄特創(chuàng)作該部小說(shuō)的時(shí)代是正處于美國(guó)工業(yè)文明迅速發(fā)展的時(shí)期,人們紛紛從農(nóng)村涌向城市,這給原生態(tài)的農(nóng)村生活帶來(lái)了巨大的影響。很多人面對(duì)城鄉(xiāng)貧富差距的日益擴(kuò)大,逐漸離開(kāi)鄉(xiāng)村去城市里追求物質(zhì)財(cái)富,并且在城市里的生活使得他們改變了原來(lái)淳樸的生活方式與精神追求。因此,小說(shuō)中年輕的禽鳥(niǎo)學(xué)家把城市里那種拜金意識(shí)帶到了鄉(xiāng)村里,喚醒了梯爾利太太的金錢(qián)欲望。當(dāng)西爾維亞想要保護(hù)白蒼鷺的鳥(niǎo)巢時(shí),她受到了別人的呵斥,還聽(tīng)到了獵人說(shuō)的要竭盡全力地去捕捉這只白蒼鷺等話語(yǔ),從而對(duì)她善良的心靈造成了不可彌補(bǔ)的傷害。這說(shuō)明了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在工業(yè)文明的吞噬下,傳統(tǒng)鄉(xiāng)土家園正在消亡。另外,小說(shuō)中還描寫(xiě)了很多農(nóng)村家庭在城市里找尋到了一定的物質(zhì)財(cái)富,但是,他們卻失去了親人等,這說(shuō)明了城市生活讓原本自然健康的身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損害與沖擊。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淳樸善良的農(nóng)民脫離鄉(xiāng)村生活后,他們的內(nèi)心變得自私、浮躁,并開(kāi)始追求經(jīng)濟(jì)利益的最大化。當(dāng)然,小說(shuō)中有一個(gè)例外,那就是女主人公西爾維亞,她是一個(gè)出生于城市的鄉(xiāng)下女孩,當(dāng)她跟隨著姥姥回到鄉(xiāng)下的時(shí)候,她感到鄉(xiāng)下真是太美了,永遠(yuǎn)都不想再回到城市里去了。這段對(duì)于西爾維亞由城市回歸鄉(xiāng)村的生活經(jīng)歷的描寫(xiě),充分表達(dá)了作家本人回歸鄉(xiāng)土家園的強(qiáng)烈意識(shí)與深切眷戀。
(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永恒追求
小說(shuō)女主人公的姓名,在拉丁語(yǔ)中意思就是森林的含義。那么,她后來(lái)跟著姥姥來(lái)到森林農(nóng)場(chǎng)生活能夠如魚(yú)得水,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她在城市中會(huì)害怕陌生人,但是在黑暗的森林中夜行卻并不懼怕。這是因?yàn)樗呀?jīng)與森林等自然環(huán)境融為一體了,她能夠爬上高高的松樹(shù)去尋找白蒼鷺的巢穴。同時(shí),她還能夠與森林中的一些動(dòng)物相處融洽。比如說(shuō),西爾維亞與森林里的一頭老牛之間就建立了一種平等而密切的關(guān)系。他們會(huì)捉迷藏,會(huì)相互追趕,他們倆在一起會(huì)度過(guò)愉快的時(shí)光。此外,這個(gè)女主人公還堅(jiān)定地抵御住了年輕鳥(niǎo)類(lèi)學(xué)家的金錢(qián)誘惑,還抵御住了可能發(fā)展的異性情誼,從而更好地保護(hù)了大自然的生態(tài)平衡,使得人與自然能夠和諧相處。事實(shí)上,作家之所以在小說(shuō)中描繪了這么多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美妙場(chǎng)景,這與她內(nèi)心深處對(duì)于人類(lèi)生命的終極思考,她對(duì)于人類(lèi)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有著永恒的追求與夢(mèng)想。對(duì)于她來(lái)說(shuō),這就是人類(lèi)獲得心靈寬慰的樂(lè)園所在。作家本人對(duì)于淳樸鄉(xiāng)土家園與綠色自然的追求,構(gòu)成了她對(duì)于故土魂?duì)繅?mèng)繞的精神追求。在她看來(lái),人們可以物質(zhì)不夠充足,但是,只要精神上是快樂(lè)、心態(tài)平和的,人類(lèi)就可以獲得一切生機(jī)和靈性,安享自然生命在和諧家園里超然的極樂(lè)狀態(tài)。
這些都充分說(shuō)明了作家對(duì)于美國(guó)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的反思,她認(rèn)為人們?cè)谧非笪镔|(zhì)財(cái)富、享受物質(zhì)財(cái)富的同時(shí),不應(yīng)該忽略了精神層面的升華與體驗(yàn),要以自然為家,而不是破壞自然,從而才能真正享受到生命的靈動(dòng)。因此,在小說(shuō)中,作家在闡釋自己對(duì)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永恒追求的創(chuàng)作主題時(shí),從三個(gè)方面表達(dá)了這種理念,即回歸自然、融入自然和感悟自然。就回歸自然來(lái)說(shuō),朱厄特認(rèn)為人類(lèi)如果能夠回歸自然,那將是一件非常浪漫、迷人且富有詩(shī)意的精神境界。因此,在小說(shuō)中,她塑造的女主人公西爾維亞,是一個(gè)出生于城市的小女孩,但是,她對(duì)家鄉(xiāng)的繁華經(jīng)濟(jì)并不感興趣,反而覺(jué)得嘈雜和擁擠。相反,當(dāng)她跟著姥姥來(lái)到鄉(xiāng)村農(nóng)場(chǎng)生活的時(shí)候,她卻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輕松與愉快,她還產(chǎn)生了永遠(yuǎn)不想回到城鎮(zhèn)那個(gè)家的愿望。在那里,她無(wú)所畏懼,還與森林里的動(dòng)物成為了好朋友。作家對(duì)于小女孩之于城市和農(nóng)村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感受,說(shuō)明了只有當(dāng)人類(lèi)與自然為伴,從城鎮(zhèn)回歸自然界,才可以過(guò)上寧?kù)o、自在的生活。那么,跟這個(gè)小女孩形成鮮明對(duì)比的人物形象就是那個(gè)來(lái)自于城市的年輕鳥(niǎo)類(lèi)學(xué)家,他離開(kāi)城市來(lái)到鄉(xiāng)村,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獲得經(jīng)濟(jì)利益,他的出現(xiàn)是對(duì)小女孩生態(tài)保護(hù)意識(shí)的極大考驗(yàn),好在小女孩最終看清了他儒雅外表下潛藏的一顆自私貪婪的心,這位鳥(niǎo)類(lèi)學(xué)家沒(méi)有姓名,這是作家故意所為,說(shuō)明了作家對(duì)這個(gè)人物的厭惡與憎恨,反過(guò)來(lái)更好地體現(xiàn)了作家本人強(qiáng)烈的生態(tài)保護(hù)意識(shí)和生態(tài)自然觀。就融入自然來(lái)說(shuō),它是指回歸自然的最高境界,是人類(lèi)與自然融為一體的美好圖景。因此,作者在給女主人公起名的時(shí)候,就融入了這樣一種理念。小女孩的名字本身就蘊(yùn)含了自然的含義,具有自然界的象征含義。
這個(gè)小女孩能夠在森林里走夜路而不感到害怕,她可以聆聽(tīng)鳥(niǎo)兒歌唱的時(shí)候感覺(jué)自己已經(jīng)進(jìn)入了夢(mèng)鄉(xiāng)等,都說(shuō)明了小女孩已經(jīng)與自然界融為一體了,她與自然之間已經(jīng)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極高境界了。中途即使出現(xiàn)了一個(gè)莽撞的鳥(niǎo)類(lèi)學(xué)家,但是,她并沒(méi)有受此影響,保持了對(duì)自然的友善和博愛(ài)。事實(shí)上,作家為什么在該部小說(shuō)中選取一個(gè)女性人物作為主要描述對(duì)象,是因?yàn)樯鷳B(tài)女性主義者一般都把自然與女性看成同類(lèi),女性與自然互為象征、互為意義,她們呼吁建立一種人與自然的平等關(guān)系,擺脫以男人為化身的人對(duì)自然以及女性的壓迫,謀求人與自然的共同協(xié)調(diào)發(fā)展。那么,人類(lèi)應(yīng)該在回歸自然和融入自然的過(guò)程中,放開(kāi)全部的感官去感受自然,才能體驗(yàn)到自然界中純凈的美。因而,朱厄特在小說(shuō)中極盡所能地描繪自然與人工環(huán)境的美妙,具有女性獨(dú)有的敏感與精致性,各種動(dòng)物似乎都充滿了靈性,能夠與小姑娘一起玩耍。尤其是小說(shuō)中小姑娘拼盡全力保護(hù)的白蒼鷺,作家更是花費(fèi)了大量的筆墨進(jìn)行描述,這只白蒼鷺有著細(xì)長(zhǎng)的脖子和迷人的身姿,讓小姑娘感到了一種極致的自然之美,并成為了它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