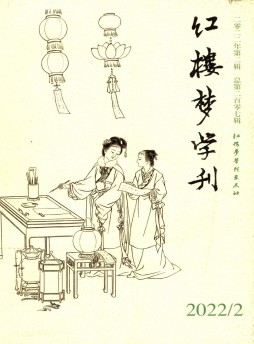紅樓夢飲食文化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紅樓夢飲食文化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引言
近年來涉及到霍譯本的譯評著作文章較重要的有肖家燕、洪濤、李晶和趙朝永等人,對兩種譯本中具體譯例的優劣得失都有所論析,如回目、人名、顏色、宗教等內容的翻譯特色及誤譯、漏譯的情況等。錢亞旭與紀墨芳于2011年發表《霍譯本中物質文化負載詞翻譯策略的定量研究》(紅樓夢學刊),從定量的角度來分析其翻譯策略;肖家燕于2009年發表《概念隱喻的英譯翻譯》,注重研究文化負載詞的隱喻。但仍不足以一一反映其細部特征,對其細節部分分析以及成因的研究稍顯不足。本文擬就從歸化與異化的角度出發對楊憲益和霍克斯所譯(以下簡稱楊譯、霍譯)《紅樓夢》中的飲食文化負載詞進行深入探討,以期探索飲食文化負載詞的有效翻譯途徑。
一、異化與歸化的內涵
韋努蒂(Venuti)在1995年提出了兩類翻譯策略:歸化(domestication)與異化(foreignization),他把這兩類策略的源頭追溯到施萊爾馬赫及其1813年發表的《論不同的翻譯方法》一文。歸化是把源語本土化,以目標語或譯文讀者為歸宿,采取目標語讀者所習慣的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異化是遷就外來文化的語言特點,吸納外語表達方式,要求譯者向作者攏。
二、《紅樓夢》楊霍譯本中飲食文化負載詞的英譯對比
1.楊霍譯本的翻譯策略。《紅樓夢》楊霍譯本的翻譯策略,也是紅譯研究的熱點之一。總的說來,楊譯采取異化的翻譯策略,基本上忠實于原文,強調把中國的文化原汁原味地傳達給譯語讀者。而霍譯本則向西方讀者靠近,采取了歸化于目的語讀者的態度,其目的是期望譯文更好的為西方讀者接受。
2.楊霍譯本的翻譯策略在飲食文化負載詞翻譯中的體現。
①千紅一窟
楊譯: Thousand Red Flowers in One Cavern
霍譯: Maiden’s Tears
楊譯似乎是中性,而霍譯文中明顯帶悲。其實,這個茶名最后一個字與“哭”諧音,所以霍將它意譯出來。“紅”在中文里也表“女性、少女”之意,楊在這里用異化把“紅”直譯成“red”,不加注釋易使西方讀者誤解為“鮮血”與“危險”。本文作者認為,楊憲益最好在第一次將“紅”翻譯成“red”時加注釋說明中英對“紅”的不同理解,這樣才能讓中國的這種文化慢慢融入西方世界。
②黃酒
楊譯:Shaosing wine
霍譯:Rice wine
黃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類之一,源于中國,且唯中國有之,與啤酒、葡萄酒并稱世界三大古酒。追溯歷史,紹興黃酒聞名古今。楊憲益將其譯為“Shaosing wine”,是用“紹興”這個地名來指代酒名,向外國讀者展示此酒有豐富的文化歷史內涵;霍克斯則將其譯為通俗易懂的“rice wine”,讀者一看即明其為何物,卻感受不到任何文化底蘊。
③掛面
楊譯:Noodles
霍譯:Vermicelli
掛面是一種細若發絲、潔白光韌,并且耐存、耐煮的手工面食,有圓而細的,也有寬而扁的。中國人喜歡吃面食,尤其在北方。遠在唐代,中國人就已經在食用這種“快餐”。楊憲益采用異化,將其譯為“Noddles”,是為了傳播中國掛面的獨一無二;霍克斯采用歸化,將其譯為“Vermicelli”,在西方飲食文化中通常表示“意面、意粉”,于外國讀者而言可減少閱讀障礙,卻無法呈現出中國文化特點。
三、楊霍譯本不同翻譯策略的影響因素
1.翻譯目的不同。影響翻譯策略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翻譯目的。翻譯目的論認為,翻譯的目的決定翻譯的原則和過程。在翻譯《紅樓夢》飲食文化負載詞時,楊氏夫婦是為了向英語讀者介紹中國飲食文化。因此,他們在翻譯過程中注重保存原著的中國飲食文化特色,而霍克斯的翻譯目的是為了滿足普通英語讀者的閱讀需要,因此注重譯本的可讀性。
2.主流翻譯理論與譯者文化不同。楊氏夫婦受到嚴復所倡導的“信、達、雅”的翻譯思想影響,同時習得漢語且受中國文化熏陶,將“信”,也就是對原文的忠實在第一位。在霍克斯所處的西方,受奈達的“動態對等”理論(Dynamic Equivalence)影響,且英語為母語,故翻譯的目的是使目的語讀者在理解和欣賞譯文時所做出的反應與原文讀者對原文的理解和欣賞所做出的反應達到最切近的自然對等。因此,我們在《紅樓夢》霍譯本中見到最多的是歸化和意譯的身影。
參考文獻:
第2篇
關鍵詞: 小說《紅樓夢》菜名翻譯策略翻譯方法
一、引言
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開始,《紅樓夢》這部“文化百科全書”即被早期的譯者節譯,但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紅樓夢》英文全譯本的出現,《紅樓夢》翻譯的研究才轟轟烈烈地展開。《紅樓夢》翻譯研究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集中在語言的層面,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受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影響,研究者們開始從多個層面從文化的視角探討《紅樓夢》的文化翻譯問題。目前,對《紅樓夢》飲食名稱翻譯研究的論文或著作還比較少,我試圖對楊憲益和霍克斯兩個全譯本中菜名的翻譯進行研究,以宏觀的角度審視兩位譯者采取的翻譯策略及翻譯方法。
二、《紅樓夢》菜名特點
《紅樓夢》這部小說中涉及的名貴菜品、粥糕點心、名茶良飲,可以說是我國傳統飲食文化的濃縮。作品中提及的美食多達57種,我將這57種食品按其命名方式分成兩大類,即含有文化寓意的命名和不含文化寓意的命名。其中不含文化寓意,以食材直接命名的食品有36種,如“燕窩湯”、“蓮葉羹”、“藕粉桂糖糕”、“鵝掌鴨信”等。含文化寓意的命名有21種,其中有包含中國風俗的命名,如“合歡湯”、“吉祥果”、“如意糕”、“壽桃”、“臘八粥”、“粽子”等;有包含中國地名的命名,如“六安茶”、“龍井茶”、“惠泉酒”、“紹興酒”等;有包含中國典故的命名,如“金谷酒”、“屠蘇酒”等;還有作者曹雪芹用“諧音寓意”手法而命名的“千紅一窟”和“萬艷同杯”。
三、《紅樓夢》菜名英譯研究
有學者研究得出,楊憲益在翻譯作品中所含的中國文化信息時,采取異化的翻譯策略,而霍克斯對此采取歸化的翻譯策略。但是具體到《紅樓夢》中飲食文化的翻譯方面,卻不能一概而論。霍克斯在飲食文化尤其是食品名稱的翻譯方面一反慣常的做法,明顯地傾向于異化的策略,這也從側面說明了中國飲食文化在全世界的地位,霍克斯在譯本中想方設法通過自己的翻譯使目的語讀者領略中國飲食文化的獨特魅力。兩位譯者在翻譯食品名稱時的具體方法詳見下列表格。
從以上表格中我們不難看出,對于小說中出現的直接以食材命名的菜肴、酒茶和糕點名稱,楊憲益和霍克斯兩位譯者總體的傾向是采用形式對等的策略,這種策略有利于原文本文化信息的傳播。直接以食材命名的菜名全文有36個,楊譯本中有34個采用了直譯的方法,而霍克斯對其中的29個進行直譯。《紅樓夢》中涉及的菜名大部分包含現實中的食材,對于這部分的翻譯,楊憲益沒有采取音譯法,而霍克斯將“小餃兒”和“楓露茶”音譯為“tiny jiao-zi”和“Fung Loo”。兩位譯者在翻譯的時候都有漏譯的現象,如楊憲益沒有翻譯“炒蘆蒿”,霍克斯沒有翻譯“風腌果子貍”和“杏仁茶”。也許是因為原著不同版本的問題,或者是譯者自身的原因,或者譯者考慮到他們畢竟是在翻譯小說,太難理解的菜名會對讀者的理解帶來障礙,所以在不影響情節的情況下省略了個別菜名的翻譯。楊憲益和霍克斯都將“面茶”譯為“breakfast”,采取了功能對等的原則,雖然指出了小說中人物當時吃的是早飯,但是沒有譯出具體的名字,從小說的角度來看,似乎對情節沒什么影響,但是無形中已經丟失了一部分飲食文化方面的信息。“面茶”作為中國的傳統食品,深受老百姓喜愛,《紅樓夢》中也多次提到,而此處譯者將它譯為“breakfast”似有不妥。
在研究過程中,我還發現,霍克斯作為有異域文化背景的譯者,雖然對原作非常喜愛,但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飲食文化的了解并不是面面俱到的,這從他誤譯的幾個菜名中可以反映出來:如“鵝掌鴨信”,霍克斯將其翻譯為“goose-foot preserve”,其實,“鵝掌鴨信”就是鵝掌和鴨舌頭,霍克斯在翻譯中沒有譯出鴨舌頭。再如“藕粉桂糖糕”,霍克斯將其翻譯為“marzipan cakes made of ground lotus-root and sugared cassia-flowers”。“藕粉桂糖糕”是江南美點之一,它的原材料是藕粉和糖桂花。但是霍克斯譯文中的“cassia”和此道點心中的“桂糖”并不是同一物質。“cassia”的英文釋義是:“It is a shrub genus in the bean family,the seed and skin of the tree can be used as flavoring.”可見與cassia對應的物質是肉桂。顯然,霍克斯將桂花和肉桂混為一談了。楊譯中的“sweet osmanthus”英文釋義是為“sweet osmanthus is native to china especially in southern china(Guizhou,Sichuan,Yunnan).It is also the‘city flower’ of Hangzhou,China.This is specialty of China.” 可見,“sweet osmanthus”與源語文本中的桂糖是同一物質。
對于含有文化信息的菜名的翻譯,楊譯較多采用直譯和音譯的方法,總體來說,楊譯還是采取異化的策略。霍譯的21個含文化信息的菜名中,除去漏譯的1個菜名之外,有10個采取的意譯,另外10個分別采取了直譯和音譯的方法。很多研究者認為,霍克斯在翻譯文化信息的時候,很明顯傾向于歸化的策略,但是對于菜名中所含文化信息的翻譯,霍克斯并沒有明顯的歸化傾向。對于小說中出現的茶和酒的翻譯,楊憲益和霍克斯均傾向于異化的策略。比如有些名茶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對應詞,形成翻譯上的詞匯空缺。對此,楊氏譯本多采用音譯加注法。通過加注,便于西方讀者了解中國茶文化。霍克斯也采取了音譯加注或者直譯的方法,使讀者了解中國文化。值得一提的是,在翻譯“六安茶”時,兩位譯者都采取了音譯的方法,但是楊憲益翻譯為“Liuan tea”,而霍克斯翻譯為“Lu-an tea”,查閱史料便可明白,霍克斯的音譯是正確的,這也顯示了霍克斯異化策略的體現,更體現了他嚴謹的態度。在翻譯“女兒茶”時,楊憲益用音譯加注的方法,而霍克斯采取了意譯“herbal tea-wutong-tips”,比較而言,楊憲益的方法在傳播文化方面更勝一籌。小說中出現的兩個“諧音寓意”——茶名“千紅一窟”和酒名“萬艷同悲”是非常難翻譯的,曹雪芹的這一創作手法是整個小說中的一大特點,但是諧音的翻譯是非常難的,甚至可以說是不可譯的,但是“諧音寓意”在小說中表達的效果可以通過功能對等的方式在譯文中體現出來。楊憲益對這兩個名稱的翻譯,都是采用直譯的手法,而霍克斯則采用了動態對等的原則,雖然這似乎不利于傳播中國文化,但是若細細品味,就能發現他的翻譯更接近于原作的寓意。翻譯是一門妥協的藝術,他這樣的“妥協”,卻收到了與原作寓意近似的效果。如 “千紅一窟”隱含那些年輕女子悲慘的命運,霍克斯翻譯為“Maiden’s Tears”,蘊含意義盡現;“萬艷同悲”也是隱喻那些年輕女子悲慘的命運,霍克斯翻譯為譯為“Lachrymae Rerum”,雖然表面看與源文本相去甚遠,可是仔細研究,就會發現譯文的絕妙之處。“Lachrymae Rerum”,意為“萬物之淚”,出自古羅馬詩人維吉爾(Virgil)的長詩《埃涅阿斯記》,“萬物之淚” 與“萬艷同悲”的深層含義是一致的,通過“眼淚”這樣的液體與原文的“萬艷同杯”之酒保持了緊密的關聯性,西方讀者通過這樣的關聯,很快便會明白作者在此處用虛擬的酒表達的意思。在含有文化信息的菜名中,楊憲益把“六安茶”翻譯為“Liuan tea”顯然是不恰當的。在此類菜名中,霍克斯卻沒有誤譯,但不知是何原因,他沒有翻譯出“金谷酒”。
綜上所述,在菜名的翻譯中,楊憲益和霍克斯兩位譯者均傾向于異化的策略,盡力保留源語文本中的文化信息。為何兩位譯者能有相同的策略傾向,究其原因,有如下幾點。首先,在《紅樓夢》的很多菜名中,食材都是現實中的物質,食材屬于物質文化,由于中英兩個民族都生活在同一物質世界里,兩種文化的共通在翻譯上的表現是選詞造句上的“偶合”現象。這使得菜名的翻譯可以最大限度地把使用異化的策略。其次,任何一部譯作,都是服務于翻譯的目的的。雖然霍克斯有著西方文化的背景,但他在翻譯《紅樓夢》時坦言特別喜歡這部小說,所以他翻譯這部小說,希望給西方讀者帶給愉悅的感受,就像他自己在讀《紅樓夢》時感受到的一樣。他當然想把小說的原貌展示給目的語讀者,只是因為文化的差異,讀者在理解方面障礙太大時,他才采取歸化的策略,至少在翻譯菜名時他采用的是這樣的處理方法。
四、結語
針對《紅樓夢》中直接以食材命名的36種食品名稱,楊憲益和霍克斯兩位譯者均采用異化的策略,翻譯方法以直譯為主。對于含有文化寓意的21種食品命名,兩位譯者也都傾向于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在翻譯的過程中,他們主要使用直譯、音譯、音譯加注、意譯等方法,各種方法的靈活使用,都是服務于一個目的,那就是最大限度地保留源語文本的信息。研究兩位譯者的翻譯,可以給我們今天的菜名翻譯帶來一些啟示:首先,菜名中的文化信息不能舍棄,應當想方設法保留。翻譯時具體可以采用直譯、音譯、音譯加注等方法還可以借助于圖片視頻等非語言媒介。其次,不僅在飲食文化,而且在其他的文化翻譯方面,異化都應該是首先選擇的策略。
參考文獻:
[1]白靖宇.文化與翻譯[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第3篇
關鍵詞:創意元素;創意與文學資源產業化的關系;創意人才的培養
中圖分類號:G1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02-0252-01
文化產業發展潛力巨大,是21世紀國家軟實力競爭的制高點。我國雖然有著5000多年的悠久的文化歷史,文學資源也是卷帙浩繁,但目前對文化尤其是對文學資源的開發不足,要想更好的發展文化產業必須充分重視創意元素在文學資源產業化中的作用。
一、何為創意
創意是文學資源產業化過程中首要和核心問題。創意本身就是一個廣為應用、極為復雜、富有多義性、不斷變化、甚至滿是矛盾的概念,幾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把那種特殊的、原創性和創意性的理念和技能稱之為創意。真正的創意是靈感和常規的、自覺的和人為的表達符號整合成的富有創造的理念,這個整合過程是難以言說的,關乎到人的原創力,甚至有神授之感。同樣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會有不同的闡釋。
創意需要促使其迸發、轉化的合適的社會土壤。所以,保護和尊重個人創造力,提供促使創意產生的寬松、自由的環境都是必不可少的條件,而歐美發達國家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是有很詳細的法律條文規定和尊重知識產權的社會共識,這是其文化產業繁榮發展的重要緣由之一,所以良好的政策環境與有效的制度設計都對創意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和決定性作用,這對于我國有著深刻的借鑒意義。
二、創意元素在文學資源產業化中的核心地位
目前創意元素在文化產業的行業涉及領域廣泛,主要體現在廣告、音樂、圖書出版、旅游產品等行業。創意元素的廣泛運用使得文化產業取得更大的成功,所以我們也要重視創意元素在文學資源產業化的核心地位。
文學資源尤其需要創意元素來發展文化產業,比如通過創意,文學名著《紅樓夢》的文化產業開發的比較成功而典型,形成的產業鏈最長,產生的經濟效益多大。在這些創意其中,影響最大的是2006年紅樓夢中人的海選活動.這個創意,以文化的名義,紅極一時的“超女”的形式,借助互聯網,電視,廣告等優勢,將觸角伸向全球,提高了活動的人氣,整個活動采用由商家冠名,電視直播,短信投票等商業化運作方式,使得《紅樓夢》未拍先火。還有其他的創意使得《紅樓夢》這一寶貴文學資源轉化為文化產業,比如說紅樓旅游和解讀紅樓一系列書籍的出版,紅樓飲食文化節,紅樓十二金釵模仿秀,紅樓年度繪畫比賽,甚至是紅樓禮品店,紅樓酒廠等。近幾年,《紅樓夢》在網絡游戲,動漫,旅游路線等方面也有創意成功的案例。
對于創意元素,我們不僅僅借鑒外國的成功經驗,而且要有創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的文化文學資源不再為中國文化產業所獨有,國際化的生產方式使得文化資源成為公共資源,這在客觀上增加了中國文化產業的危機感。美國迪斯尼公司利用中國文學素材拍攝動畫大片《花木蘭》。其中許多場景運用了中國元素,整個影片中都在體現濃郁的中國風味。如寫意朦朧的潑墨山水畫風格改寫了西方慣用寫實的油畫表現效果,這在迪士尼的動畫電影中前所未有的。這一創意,為美國在全球搶走3億432萬美元票房。這些都不得不令我們反思,中國不缺乏文化資源,不缺乏設計師,但缺乏有創新意識的人才。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我們應該更加重視創意元素在中國文化產業中的核心作用。
三、創意人才的培養
在文化產業中,文化是土壤,創意是種子,產業是果實。我國文化創意產業中很少自主擁有核心技術,未能將中國博大精神的傳統文化充分的利用起來,在文化創意產品制作上缺乏想象力,所以制作出來的產品往往雷同性高,無法滿足廣大消費者的需求。我們要培養全民的創新意識。從思想意識方面鼓勵群眾多創新,多點子,少模仿。其次,注重培養創意專業人才。不僅需要創意產業鏈上游的設計人才、創意策劃人、建筑師等,而且需要創意產業鏈下游的管理人員與市場營銷人員。這里可以借鑒美英等發達國家的經驗,有關部門和機構推出或籌備創意人才培訓項目,培養一批有創新思維、善于運用先進技術、能夠設計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原創作品的創意人才。
面對全球制造業中心的轉移及“中國設計”時代的來臨,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更應該重視設計人才培養和技術創新等體系的構建。霍金斯認為“創意經濟的基礎是那些使用自己的想像力、夢想和幻想的人。
總的來說,創意是整個文化產業的靈魂和生命,只有好的創意才能更好的將文學資源轉變成經濟效益,促進文化產業發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