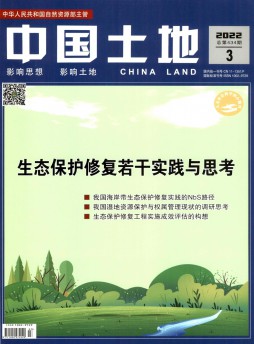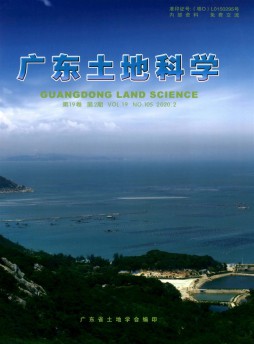土地家庭承包制度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土地家庭承包制度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土地家庭承包制度是一項經濟制度的創新,一種制度的創新和運行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的作用是巨大的,國內外學者對制度創新理論研究成果已很多。當代新制度經濟學大師道格拉斯.C.諾斯(DouglassC.North)指出制度經濟學的目標是研究制度演進背景下人們如何在現實世界中做出決定和這些決定又如何改變世界的。科學技術的進步對經濟的發展雖然起重要作用,但真正起關鍵作用的是制度,包括所有制、分配、機構、管理、法律政策等(諾斯,1994);諾斯和湯瑪斯又認為“提供適當的個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徐漢明,2004)。
1984年至1996年,是對土地家庭承包制度的正績效研究評價集中時期。此時國內外學者對制度的績效評價是一致的稱贊與肯定的,主要從制度產生的結果:結束了中國長期農產品短缺歷史、用世界上7%的耕地養活著世界上22%的人口。此外,主要觀點如認為土地使用制度的變遷是漸近的,土地使用權回歸于農民,激發了農民生產勞動的積極性,提高了土地生產力水平,體現了制度的效率與公平(曲福田,1999;林善浪,1999;林毅夫,1999;張宏宇,1999);家庭承包經營制從根本上否定了體制及其體制下的勞動監督和激勵不足問題,使即將陷入崩潰的農村經濟擺脫了困境,促進了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該制度適合農業生產特點,有利于農民因時因地制宜進行生產,激活了農村沉睡多年的生產力,降低了制度變遷的成本,解決了集體統一經營時期勞動過程中的“搭便車”和監督問題,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的高速增長,有利于推動國民經濟的增長(張永麗,2002;楊德才,2002;滿莉,2002等),是我國建國之后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張孝德,2001);等等。這些研究多從宏觀方面對制度的激勵作用和社會效果進行了肯定,并對制度的變遷定義為誘致性變遷,產生的是“帕累托”效應。但對土地使用權回歸農民,農民如何運用權利、制度激勵的關鍵點等微觀研究則較少。
1996年以來主要是對家庭承包經營負績效方面的評價與研究。自1996年后,農產品生產進入供需平衡豐年有余時期,市場農業的要求與傳統型家庭經營的不適宜性及“三農”問題的日益顯化,人們對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優越性研究轉向局限性分析。認為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局限性表現:一是產權界定不清問題。承包制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農業產業化要求相矛盾,農民應有的權益得不到保障(張榮,2002);二是稅費負擔過重,影響經營效益。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性質不明確,農民增產不增收(國風,2003),農民稅費負擔嚴重,影響了農民利用土地的積極性,制度效率降低(戚名琛,1996;沈守愚,1997;韓俊,1999;徐漢明2004;);三是土地規模問題。對此問題的研究成果很多,如農村土地按人均分配,細化了農地的經營,不利于土地的規模經營效益(曲福田,2001,楊德才,2002;)。2004年前,稅費制度不健全,農民經營土地除負擔國家規定的“三提五統”外,以承包土地面積為依據的地方政府攤派現象嚴重,致使農民種地負擔過重,此時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減輕農民負擔方面;2004年河北省開始按比例逐年降低稅費額,到2006年全國取消農業稅。目前,農民經營土地進入了種地無費無稅時代。同時,國家生產直接補助政策使農民種地不但無稅,而且有補助,對穩定土地經營起到了促進作用,再次提高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但對小規模經營起了固化作用,也影響了土地流轉速度,這是稅費改革后的正負影響評價。以上進行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度的局限性研究有利于制度深化改革或完善,但對農民是否接受或如何實現規模經營等,還需要傾聽農民的想法,尋找宜于農民自愿選擇的途徑。
二、土地家庭承包經營方式的研究及內容
土地家庭經營,國內外歷史久遠。根據歷史發展階段、社會制度及國家或地區的自然稟賦不同,家庭經營方式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發展,其研究內容也不斷豐富。經濟學家T.舒爾茨在上世紀60年代提出,最重要的手段,一是市場機制,通過農產品和生產要素的價格變動來刺激農民;二是對農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亦即教育培訓”(T.舒爾茨,1964)。日本人多地少,家庭經營規模小,農業處于衰退趨勢,由買賣實現土地轉移和規模經營非常困難,政策走向是以租佃來促進土地流轉以提高家庭經營土地的效率(關谷俊作:《日本的農地制度》,金洪云譯,2004);發達國家高科技在農場中廣泛應用,但產品單一化,農場主家庭主要收入來源已不是農場(胡芳,2006);林毅夫1988年在其《中國農業家庭責任制改革的理論與經驗研究》中提出:中國的生產隊集體耕作制度不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勞動監督非常困難,社員的勞動積極性相應地很低。相反,家庭農場的優越性在于農民為自己生產,因此生產的積極性也就高。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家庭承包經營規模小而效益低的問題已很明顯。多數學者提出實施規模經營、合作經營是土地使用制度深化改革方向之一。但我國目前尚不具備實現土地大規模經營的條件。目前探索實施的土地規模經營方式有政府主導型、市場主導型和政府和市場互補型三種類型,其中,市場主導型是我國土地規模經營的必然選擇(葉淇等,2005);對于整個農業而言的資本稀缺,可以采用外部合作經營模式,引進外部工商業資本,通過工商業資本對農業的滲透、通過農業產業化的發展來彌補;混合經營模式是內部合作經營模式與外部合作經營模式的混合體,這一模式既采用內部合作經營模式,組成農戶的合作社,實現資本積聚,又采用外部合作經營模式,引進外部工商業資本,通過工商業資本對農業的滲透,通過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彌補資本的稀缺性(于洋,2005)。但在短期內我國農村能否實現規模經營,農民是否意愿擴大經營規模,是我們需要從實踐中深入探索研究的問題。
建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用技術、信息等服務將農民聯合起來,發展市場農業,是農村土地經營發展的方向(馮開文,2003);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解決小農戶大市場的矛盾(趙繼新,2004);降低風險,合作組織的業務必須限于向其成員開放(Faust,1997);分析研究我國農民的合作化運動史,為今日農村土地合作方式提供借鑒(羅平漢,2004);關于合作組織模式大體上可以分為四種:一是市場帶動型。以市場為導向引導和帶動農戶組織化經營;二是龍頭企業牽動型。龍頭企業一邊連著基地、農民,另一邊連著市場,對市場反應敏感,而且可以提高農產品質量和市場競爭力,并把工業或商業利潤留在農業領域;三是生產基地啟動型。通過生產基地的輻射作用,使得我國農業產業化成為可能;四是經濟組織推動型,這些年來在農業生產專業化、基地化的發展過程中,農村各地形成了一大批合作經濟組織,它帶有生產協作性和服務性。因此,它既是家庭生產經營的自然延伸,又為農業產業化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最終,這四種模式就構成了在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下的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前提條件(王樹祥,2004)。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需要進行土地使用制度或經營方式的深化改革與創新途徑研究。
三、土地家庭承包經營中勞動力轉移因素及趨勢
關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的研究,國外比較成熟的理論有多種,如拉文斯坦(E.G.Ravenstein)的遷移理論、劉易斯(W.A.Lewis)的二元經濟理論、拉尼斯和費景漢(G.Ranis-J.Fei)的二元經濟模式以及雷文斯坦(E.G.Ravenstein)的推拉理論等。國內主要從影響勞動力轉移的因素、勞動力轉移的模式及轉移中的問題等開展了多方面的研究。
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因素研究有:經濟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因素之一,區域經濟發展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分為經濟發展水平因素和經濟結構因素。具有較低務農收入的農民最有可能做出轉移決策,相對收入差距是農村勞動力轉移決策的重要影響因素(蔡昉,2001);教育因素和社會文化因素都會對勞動力轉移產生影響(張林秀,1999;趙耀輝,2001);在勞動力轉移中,年齡與轉移概率的關系是倒U型的。女人較男人不喜歡轉移。已婚使轉移概率降低2.8%,對這種結果的首要解釋是已婚的勞動者具有較高的轉移成本(包括現金成本和心理成本)(趙耀輝,1998,朱農,2002)。
對于農村勞動力轉移模式的研究國內已有很多,大體分為五種模式:第一種是“離土不離鄉”模式。該轉移模式突破了西方發展經濟學家提出的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部門轉移的“二元”模式,形成了一種“三元”模式。實行農業產業化是轉移為數眾多的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需要(陳吉元,1996);第二種模式是“離土離鄉”模式。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從根本上的轉移,它符合產業發展演化的規律和現代世界的城市化潮流,是目前土地使用制度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理想模式(郭盛昌,1997);第三種模式是“不離土不離鄉”模式。倡導通過農村自身的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增加農村就業門路。(陸銘,1998);第四種模式是小城鎮模式。小城鎮吸納勞動力的費用較少,因此發展小城鎮是解決我國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的根本出路(李寶庫,1997);第五種模式是“離鄉不離土”模式。由于土地關系的存在,農民一般進城但是不定居的轉移形式,目前就地轉移勞動力遷移意愿的實證研究發現,有91.53%的勞動力都明確表示,若向城市遷移需放棄土地,他們是不會做出遷移決策的(陳欣欣,2001);等等。為什么農民可以從農村、從土地上遷移或流轉出來,而且家庭用于土地經營的勞動力仍然處于下降趨勢中,且男勞動力下降幅度和速度快于女勞動力,但他們仍然不愿放棄土地,其原因需要我們做進一步深入探究。
關于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績效的研究內容是多方面的,其綜合較一致性的研究觀點是認為該制度為中國農村經濟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對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制度需要不斷完善,應在穩定土地家庭承包制的基礎上進行經營方式的創新,健全勞動力合理有序轉移機制,使該制度在經濟建設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發揮持續性作用。
擴展閱讀
- 1土地調查落實計劃
- 2土地糾紛
- 3土地資源及土地經營分析
- 4土地財政與土地城鎮化互動關系
- 5集體土地
- 6土地巡查報告
- 7土地買賣合同
- 8農業土地流轉研究
- 9農村土地流轉分析
- 10探索土地流轉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