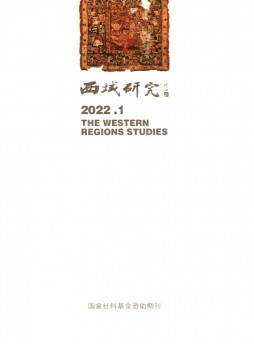西域和中亞絲綢之路的經(jīng)營方略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西域和中亞絲綢之路的經(jīng)營方略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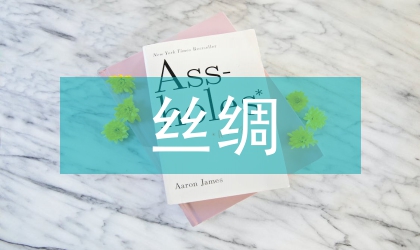
《甘肅社會科學(xué)雜志》2015年第四期
明朝初建后,西域中亞絲綢之路段活躍著蒙古后裔東察合臺汗國分裂形成的大小部落割據(jù)政權(quán)和中亞蒙古突厥后裔建立的帖木兒帝國,這些政權(quán)與新建立的明朝關(guān)系疏遠(yuǎn),有的懷疑明朝,有的藐視明朝,還有的與之抗衡,希望有朝一日能重歸中原。但是西域中亞是絲綢之路通過的重要地區(qū);絲路興,王朝興,絲路衰,王朝衰,自從張騫開通絲綢之路以后,凡是統(tǒng)一的中央政權(quán)都十分重視對絲綢之路的經(jīng)營,明朝也不例外。迫于絲綢之路的重要性,面對蒙元后裔控制西域中亞絲綢之路的態(tài)勢,太祖成祖父子兩代審時度勢,深思熟慮,積極主動與西域中亞各個部落政權(quán)和國家建立聯(lián)系,盡其所能經(jīng)略絲綢之路,以保證中原王朝與西域中亞絲綢之路沿線部落政權(quán)和國家貢使關(guān)系的建立和經(jīng)濟(jì)交往的繼續(xù),延續(xù)沿途各民族文明交流和文化發(fā)展的歷史。學(xué)界有關(guān)明代絲綢之路的研究處于觀念拘泥現(xiàn)狀,認(rèn)為明代閉關(guān)自守,絲綢之路經(jīng)濟(jì)、文化交流成效甚微。筆者撰寫《通向遠(yuǎn)方的路———明清時期絲綢之路文化交流》一書時,閱讀了相關(guān)明史和中亞文獻(xiàn)資料,深感學(xué)界認(rèn)識的局限和偏頗。明襲元而建后,太祖成祖兩代苦心經(jīng)略絲綢之路,并取得良好成效,恢復(fù)了絲綢之路西域中段經(jīng)濟(jì)、文化交流,絲綢之路暢通無阻,其功勞理應(yīng)受到重視。本文就明太祖成祖經(jīng)略絲綢之路采取的一系列策略,明前期西域中亞絲綢之路局勢以及這一時期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特殊性進(jìn)行研究,以補(bǔ)充學(xué)界認(rèn)識之不足。
一、建立絲綢之路河西走廊西段防御體系,防范北方蒙古和西域蒙古后裔部落政權(quán)南下東進(jìn),保證了絲綢之路河西走廊段的暢通
明朝建立后,天山南北、伊犁河谷的大大小小割據(jù)政權(quán)互不統(tǒng)屬,各自為王,明朝稱其“地大者稱國,小者止稱地面”[1]。他們或者結(jié)盟,或者互相攻訐。在宗教信仰方面,已經(jīng)完成了伊斯蘭教化的過程,繼續(xù)著文化的再生和重組。而蒙古西部一些地方到新疆北部阿爾泰山和額爾齊斯河一帶被蒙古瓦剌人占據(jù),他們時刻覬覦天山南北和中亞絲綢之路,圖謀南下控制該地。西域中亞絲綢之路段民族和宗教關(guān)系發(fā)生著深刻的變革。面對蒙古部族在明朝北部、西部的強(qiáng)大壓力,絲綢之路河西走廊西端成為明朝防范西北蒙古勢力的戰(zhàn)略要地,為加強(qiáng)該地防守,明太祖仿照漢武帝治理策略,在絲綢之路河西走廊西部和北部建立邊界防線,北阻蒙古,南捍諸番。經(jīng)過太祖成祖父子兩代,基本完成該地軍事部署。北方設(shè)沿邊九鎮(zhèn),西北設(shè)關(guān)西諸衛(wèi)。沿邊九鎮(zhèn)最西端甘肅鎮(zhèn)承擔(dān)護(hù)衛(wèi)絲綢之路,防范河西走廊北部西域蒙古南下和東進(jìn)的戰(zhàn)略任務(wù)。《明史?兵志?邊防》云:“終明之世,邊防甚重。東起鴨綠,西抵嘉峪,綿亙?nèi)f里,分地守御。初設(shè)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zhèn),繼設(shè)寧夏、甘肅、薊州三鎮(zhèn),而太原總兵治偏頭,三邊制府駐固原,亦稱二鎮(zhèn),是為九邊。”
關(guān)西諸衛(wèi)承擔(dān)防守西域中亞蒙古和青海蒙古的任務(wù)。關(guān)西諸衛(wèi)在絲綢之路河西走廊西端與西域接壤沿邊地帶,即從漠西蒙古到瓜州再到柴達(dá)木盆地邊緣沿線。當(dāng)時這里住牧著大大小小的內(nèi)附蒙古、回回、撒里畏兀兒、畏兀兒人、哈剌灰等部族,明太祖成祖根據(jù)情勢,因俗施治,封官安置部族首領(lǐng),讓他們分別擔(dān)任衛(wèi)、所指揮,這樣在此地段形成了由內(nèi)附蒙古族和其他少數(shù)民族組成的人力長城。這道人力長城,是防衛(wèi)西域乃至中亞蒙古勢力東進(jìn)的一道天然屏障。正如《明史?西域傳》記載,諸衛(wèi)可以“內(nèi)附肅州,外捍達(dá)賊”。關(guān)西諸衛(wèi)的設(shè)置既保證了內(nèi)附少數(shù)民族的生存困境,也避免了西域蒙古后裔地方政權(quán)的東擴(kuò)以及漠西蒙古族和南部吐蕃以及其他民族聯(lián)為一體,對明朝形成威脅的可能性,減輕了河西走廊西端絲綢之路的邊防壓力。正如明正德四年(1509年)兵部所言:“西戎強(qiáng)悍,漢、唐以來不能制。我朝建哈密、赤斤、罕東諸衛(wèi),授官賜敕,犬牙相制,不惟斷匈奴右臂,亦以壯西土藩籬。”[2]如《明史》所言,使西番、北蒙兩不相通,邊疆永無虞,國家固如磐石。北方沿邊九鎮(zhèn)之一的甘肅鎮(zhèn),防衛(wèi)體系和關(guān)西諸衛(wèi)防衛(wèi)體系相連接,有效防范了青藏高原北部腹地蒙古、吐蕃以及北方漠西蒙古和西域、中亞蒙古后裔割據(jù)政權(quán)的北上、南下和東進(jìn),保證了絲綢之路河西走廊段各民族經(jīng)濟(jì)文化交流的暢通。這條防衛(wèi)體系的建立是特殊時期的特殊策略,僅僅是軍事上的防衛(wèi),并沒有隔斷明王朝與西域中亞以及河西走廊各民族與西域中亞的交往,相反使絲綢之路上的經(jīng)濟(jì)和文化交流得到安全保障。大批西域中亞商人通過玉門關(guān)到河西走廊和中原貿(mào)易,有的居留在河西走廊沿線,人數(shù)增加,開始形成新的民族,即穆斯林民族共同體。
二、安撫哈密地方政權(quán),確保絲綢之路西域門戶敞開
絲綢之路出玉門關(guān),哈密是沿線第一個人口集中、商貿(mào)發(fā)達(dá)的重鎮(zhèn)。明朝定鼎中原后,這里是東察合臺汗王后裔兀納失里建立的政權(quán),其扼守絲綢之路要沖,控制西域和明朝交往的咽喉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當(dāng)時,哈密作為蒙古后裔建立的地方政權(quán),對明朝的態(tài)度是藐視且抵觸。哈密王借地理優(yōu)勢,時常騷擾明朝邊鎮(zhèn)和周邊地方政權(quán),成為明朝與西域中亞之間通商通使的一大障礙。通西域,必須解決哈密問題。面對哈密的騷擾和在商道上的劫掠行徑,明太祖曾兩次用兵哈密,通過武力使哈密臣服。之后,又安撫有加,封王賜官,使哈密成為明朝的附庸。
洪武十三年(1380年),太祖第一次用兵哈密,派遣“都督濮英練兵西涼,請出師略地,開哈梅里之路以通商旅。太祖賜璽書曰‘略地之請,聽爾便宜,然將以謀為本,爾慎毋忽’。英遂進(jìn)兵。兀納失里懼,遣使納款。明年五月遣回回阿老丁來朝貢馬。詔賜文綺,遣往畏吾兒之地,招諭諸番”。這是明朝首次用兵哈密。此次用兵,兀納失里表示臣服,但這種臣服是一種表面行為,實際上仍數(shù)次打劫往來商隊,甚至扣押西域各部向明王朝朝貢的使團(tuán),繼續(xù)威脅絲綢之路的商路安全。隨著明朝軍事勢力的增強(qiáng)和中原北部的安定。洪武二十三年(1391年)四月,明太祖令涼州衛(wèi)指揮使宋晟與陜甘都督劉真合兵,第二次出兵哈密,兀納失里出逃。之后不久兀納失里返回愿意臣服明朝。繼續(xù)承襲肅王封號,鎮(zhèn)守哈密。明朝和哈密關(guān)系的穩(wěn)定,保證了絲綢之路的暢通和安全,從此哈密擔(dān)負(fù)起過往商旅和貢使接待事宜。《明實錄》記載“每歲各處回回進(jìn)貢者至此,必會少憩,以館款之。或遏番寇劫掠,則人馬可以接護(hù)”。之后,西域諸夷者凡三十八國通過哈密到達(dá)京城,貢使與商貿(mào)往來絡(luò)繹不絕。太祖收服哈密與其用兵北方蒙古取得勝利有關(guān)。洪武二十年(1388年)正月,太祖任馮勝為征虜大將軍,潁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lán)玉為左右副將軍,率兵二十萬遠(yuǎn)征遼東,大獲全勝,俘獲降眾二十萬人,另獲馬駝牛羊十五萬余,所謂“牛羊馬駝輜重互百余里”。此次遠(yuǎn)征規(guī)模顯示了明朝兵威之盛已遠(yuǎn)播漠北,沉重打擊了北部蒙元殘余勢力。明朝定鼎中原后勢力威震域內(nèi)外,令周邊四鄰刮目相看。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洪武二十三年(1391年)四月,明朝在涼州備兵,征討哈密,將哈密問題徹底解決。明朝用兵遼東,再次征討哈密的軍事行動使西域中亞蒙古后裔部族及其他部族徹底轉(zhuǎn)變了對明朝的態(tài)度,一改過去輕慢不服為主動承認(rèn)明朝中央政權(quán),有的紛紛歸附,有的愿意通商通使朝貢,通往西域中亞的絲綢之路門戶徹底被打開了。
到成祖時期,哈密形勢發(fā)生變化,內(nèi)部權(quán)力爭斗,外部北邊瓦剌和西邊吐魯番等干涉內(nèi)務(wù),使哈密左右為難,腹背受敵。永樂元年(1403年),兀納失里去世,弟安克帖木兒繼位,此時明朝國力強(qiáng)盛,安克帖木兒已經(jīng)不敢與明朝對抗,西邊吐魯番東擴(kuò)造成的壓力,迫使安克帖木兒越來越愿意內(nèi)附明朝。明成祖冊封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永樂三年(1405年),安克帖木兒去世,侄子脫脫繼王位,脫脫自幼在中原長大,在哈密地位并不穩(wěn)固,遭其祖母驅(qū)逐。面對此情形,成祖著手解決哈密亂局。成祖利用哈密政權(quán)內(nèi)部親明勢力,一舉收服哈密。永樂四年(1406年)三月,設(shè)立哈密衛(wèi)。脫脫仍繼王位,并封其部落頭目為指揮使等職,派遣明朝漢官輔佐。哈密衛(wèi)的設(shè)置,穩(wěn)固了明朝通向西域中亞的通道,之后哈密衛(wèi)在明朝護(hù)衛(wèi)下,發(fā)揮絲綢之路咽喉作用,為來往貢使和商賈提供休憩和護(hù)衛(wèi)之職責(zé)。
三、積極主動派遣使者,與絲綢之路天山北麓別失八里政權(quán)建立友好關(guān)系
沿哈密西行,占據(jù)絲綢之路天山北麓地帶影響較大的政權(quán)是別失八里。“別失八里,西域大國也。南接于闐,北連瓦剌,西抵撒馬兒罕,東抵火州,東南距嘉峪關(guān)三千七百里。或曰焉耆,或曰龜茲。元世祖時設(shè)宣慰司,尋改為元帥府,其后以諸王鎮(zhèn)之。”[4]別失八里是元朝察合臺后裔分裂形成的地方政權(quán),即東察合臺政權(quán)的一部分。明初占據(jù)著絲綢之路天山北麓到伊犁河谷一帶,這是絲綢之路要沖之地,此時的別失八里處于民族宗教變革時期。早在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太祖曾遣使持詔諭云南、八番、西域、西洋、爪哇、蒙兀兒等地:“朕憫生民之涂炭,興舉義兵,攘除亂略,天下兵民尊朕居皇帝位,國號‘大明’。建元洪武。前年克取元都,四方以次平定。其占城、安南、高麗諸國,俱已朝貢。今年遣將巡行北邊,始知元君已歿,獲其孫買的里八剌,封為崇禮侯。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民成樂其所。又慮汝等僻在遠(yuǎn)方,未悉朕意,故遣使者往諭,成使聞知。”詔諭頒布后,西域地方政權(quán)除撒里畏兀兒、安定王避坎遣使朝貢之外,其他大小政權(quán)均無遣使來朝者。通絲路,就得與別失八里建立聯(lián)系。與其建立聯(lián)系意義重大,一是擴(kuò)大明朝在西域的影響,二是打通絲綢之路天山北麓通道。太祖采取派遣使者主動通好的策略,與別失八里建立聯(lián)系。洪武二十四年(1392年),哈密問題解決后,太祖迅速派蒙古貴族后裔寬徹赴西域,詔諭西域諸部,闡述明朝立場,意欲建立通使關(guān)系。寬徹到西域后,被別失八里國王黑的兒火者拘留,并以此要挾,提出人質(zhì)交換條件。
所謂人質(zhì)事件指的是在洪武初年,寄居甘肅、陜西絲綢之路沿線的西域中亞商人,被明朝充當(dāng)使臣派遣出使西域諸國,為了牽制這些人,其家屬仍留甘州、涼州等地。還有一些在邊境劫掠,被明朝邊將俘獲的別失八里人。這部分人口集中分布在河西走廊甘州和涼州,坊間盛傳其有間諜行為,明太祖將其徙居揚州,遠(yuǎn)離商道。這些人徙居揚州后,伺機(jī)返回。此后太祖詔諭甘肅都督宋晟等:凡西番回回來互市者,止于甘州、肅州城外三十里,不許入城。朝貢使臣不受限制。別失八里王要求明朝釋放的人質(zhì)正是這部分人。經(jīng)過寬徹等人的談判,雙雙交換人質(zhì),寬徹等人回到明朝。通過人質(zhì)交換一事,明朝和別失八里初步建立聯(lián)系。之后,寬徹利用自身蒙古貴族后裔身份又赴西域游說,宣傳明朝外交政策,取得了別失八里的了解和信任,表示愿與明朝通使通商,建立友好往來。其他一些小部落政權(quán)也紛紛表示愿意與明朝建立貢使關(guān)系。和別失八里關(guān)系的建立,意味著明朝在絲綢之路天山北麓影響的擴(kuò)大,也意味著明朝中央政權(quán)得到西域多數(shù)地方割據(jù)政權(quán)的承認(rèn),之后一些小的地方割據(jù)政權(quán)相繼與明朝建立了聯(lián)系。
明朝對西域中亞地方政權(quán)的懷柔策略,還體現(xiàn)在其優(yōu)禮伊斯蘭教方面。明朝建立之際,正值伊斯蘭教向西域興盛傳播時期,絲綢之路西域中亞段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特點是伊斯蘭教迅速傳播,西域中亞蒙古貴族和其他信仰佛教的民族經(jīng)歷了伊斯蘭教化的過程。受伊斯蘭教傳播影響,也鑒于與西域中亞等地關(guān)系的建立,明太祖尊重西域中亞各個部族的伊斯蘭教化,禮遇伊斯蘭教。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在明朝機(jī)構(gòu)設(shè)置中,改太史院為司天監(jiān),其內(nèi)部特別設(shè)置回回司天監(jiān),專門負(fù)責(zé)回回事宜。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征召元朝回回歷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南京,了解伊斯蘭教歷法,并封官賜予財物。此后鄭阿里等專門負(fù)責(zé)回回司天監(jiān)事務(wù)。明成祖永樂五年(1407年),專設(shè)四夷館翻譯少數(shù)民族語言,“四夷館在東華門外,南向。設(shè)太常寺少卿提督之,聽于翰林院。所隸凡八館:曰西天,曰韃靼,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裔”[6]。八館以西域中亞少數(shù)民族語言為多,顯示出明朝重視與西域中亞的關(guān)系以及西域中亞對明朝的影響。這也是明朝在宗教方面孤立信仰藏傳佛教蒙古族的策略。明成祖時期國力強(qiáng)盛,成祖認(rèn)識到絲綢之路天山北麓地理通道的重要性,十分重視與別失八里的關(guān)系,繼續(xù)太祖時期與別失八里的友好交往,貢使和商貿(mào)不絕于路,交往更加頻繁。清代學(xué)者引用前朝記載時感慨道:“洪武中,太祖欲通西域,屢遣使詔諭,而遐方君長未有至者。”“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萬方,遣使四出招徠。由是西域大小諸國莫不稽顙稱臣,獻(xiàn)琛恐后。又北窮沙漠,南極溟海,東西抵日出沒之處,凡舟車可至者,無所不屆。”
四、與中亞帖木兒帝國建立聯(lián)系,促進(jìn)絲綢之路中亞貢使商貿(mào)發(fā)展
太祖成祖鎮(zhèn)服哈密,懷柔別失八里的策略基本解決了絲綢之路西域段問題,繼續(xù)向西,到額爾齊斯河以南偏西便進(jìn)入中亞地區(qū),這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區(qū)域,也是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中心區(qū)域之一。當(dāng)時出伊犁河谷之后進(jìn)入中亞的絲綢之路段由有蒙古和突厥血緣的西察合臺汗國帖木兒掌控。洪武三年(1370年),帖木兒經(jīng)過三十年征戰(zhàn),戰(zhàn)勝周圍部族建立占據(jù)中亞要害位置河中地帶的帖木兒帝國,帖木兒帝國疆域遼闊,堪與明朝抗衡,是蒙古帝國滅亡后在西域中亞活動的蒙古后裔所建立的最大的政權(quán)。帖木兒帝國晚明朝兩年建立,從洪武元年明太祖發(fā)往各地的詔諭沒有提及帖木兒帝國可知,帖木兒尚沒有立國。帖木兒路途遙遠(yuǎn),雙方建立聯(lián)系比較晚,彼此關(guān)系以帖木兒率先示好開始。洪武二十年(1360年),帖木兒第一次派遣使者赴明朝,“二十年九月,帖木兒首遣回回滿剌哈非思等來朝,貢馬十五,駝二。詔宴其使,賜白金十有八錠。自是頻歲貢馬駝”。洪武二十五年(1365年),帖木兒第二次派遣使者到明朝,“兼貢絨六匹,青梭幅九匹,紅綠撒哈剌各二匹及鑌鐵刀劍、甲胄諸物。而其國中回回又自驅(qū)馬抵涼州互市。帝不許,令赴京鬻之”。帖木兒主動與明朝建立關(guān)系,影響中亞西域其他政權(quán)效仿,紛紛派遣使者和商貿(mào)團(tuán)體到明朝貿(mào)易,以至于人數(shù)多到明朝不得不采取限制措施。他們集聚肅州,等候通關(guān)牒文,有時候明朝不得不采取遣散辦法,遣散不少商人回去,其中一次遣散“歸撒馬兒罕者千二百余人”。洪武二十七年(1367年)八月,帖木兒第三次派遣使者到明朝,貢馬二百,并呈表一封,表文極盡恭維之詞。“恭惟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統(tǒng)一四海,仁德洪布,恩養(yǎng)庶類,萬國欣仰。
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運數(shù),為億兆之主。光明廣大,昭若天鏡,無有遠(yuǎn)近,咸照臨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聞圣德寬大,超越萬古。自古所無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皇帝皆服之。遠(yuǎn)方絕域,昏昧之地,皆清明之……今又特蒙施恩遠(yuǎn)國,凡商賈之來中國者,使觀覽都邑、城池,富貴雄壯,如出昏暗之中,忽睹天日,何幸如之!又承敕書恩撫勞問,使站驛相通,道路無壅,遠(yuǎn)國之人咸得其濟(jì)。欽仰圣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國中部落,聞茲德音,歡舞感戴。臣無以報恩,惟仰天祝頌圣壽福祿,如天地永永無極。”[11]表文表現(xiàn)出帖木兒對明朝的首肯和敬仰,表示愿意與明朝建立友好往來的貢使商貿(mào)關(guān)系。帖木兒表文令朱元璋深受感動,贊賞其文采。之后,“其貢馬,一歲再至,以千計,并賜寶鈔尚之”。鑒于帖木兒幾次派遣使者,主動示好,太祖對遙遠(yuǎn)的帖木兒心懷疑慮,于是在帖木兒第三次派使者赴明朝后,太祖派遣使者傅安出使中亞,探究虛實,這是明朝建立后第一次派遣使者赴中亞出訪。傅安到達(dá)中亞后,帖木兒扣押傅安一行。太祖對帖木兒的疑慮是正確的,其遣使明朝并沒有建立傳統(tǒng)貢使關(guān)系之意,扣押傅安等人就是明證。遣使友好是假,蓄謀東向取代明朝是真。果然到永樂三年(1405年),帖木兒率兵二十萬,東侵明朝,不幸的是病死途中,只得罷兵。此次東進(jìn)失敗,帖木兒帝國元氣大傷,帝國與明朝的關(guān)系徹底改善。帖木兒去世后,內(nèi)部權(quán)力爭斗激烈,帝國割據(jù)分裂。明成祖抓住機(jī)遇,主動派遣專使攜帶文書、文綺、彩幣前往帖木兒,但處于權(quán)力紛爭時期的帖木兒帝國并沒有對明朝表示友好。直到帖木兒第四子沙哈魯掌控帖木兒帝國后,將撒馬爾罕分賜其子兀魯伯,其將政治中心遷往哈烈(駐哈烈,今阿富汗西北部之赫拉特)。沙哈魯主動與明朝修好,派遣使者送傅安一行返回。之后帖木兒后裔分裂政權(quán)最有影響的哈烈(正統(tǒng)繼任者)和明朝建立了真正意義上的貢使友好關(guān)系。
帖木兒帝國與明帝國版圖相差無幾,兩個政權(quán)之間的交往是平等的,對明朝而言,為保證絲綢之路西域中亞通道暢通是其交往的目的;對帖木兒而言,初期與明朝交往有恢復(fù)蒙元統(tǒng)治,重振往日雄風(fēng)的夢想。最初帖木兒恭維明太祖,主動遣使,一是了解明帝國虛實,二是基于通商考慮。到成祖時期,帖木兒東擴(kuò)失敗后,帖木兒分裂割據(jù),其子在哈烈建立的政權(quán)才與明朝建立起了真正意義上的通使商貿(mào)關(guān)系。此時成祖一方面與哈烈積極建立頻繁的商貿(mào)關(guān)系,一方面派遣使者到中亞出訪。此后明朝和帖木兒關(guān)系一直比較穩(wěn)定。在與中亞帖木兒關(guān)系穩(wěn)定后,雙方的商貿(mào)也得到發(fā)展。成祖時期,中亞商人對到明朝做生意夢寐以求,所謂“蓋番人善賈,貪中華互市,既入境,則一切飲食、道途之資,皆取之有司。雖定五年一貢,迄不肯遵,天朝亦莫能難也”[13]。凡來華經(jīng)商的西域中亞商人,一經(jīng)進(jìn)入明朝管轄區(qū)域,沿途各個驛站便提供食宿,對這些商人而言,到明朝做生意真是一本萬利的事情。明朝通商方面的優(yōu)惠政策吸引了中亞商人,帖木兒商人接踵而至,成為中亞各個邦國中來明朝人數(shù)最多的國家。從洪武到萬歷時期,帖木兒和明朝雙方通商貿(mào)易沒有中斷過,據(jù)《明實錄》等書記載:自洪武年間至萬歷九年(1581年),帖木兒派來的朝貢使團(tuán)多達(dá)五十余次,明朝從洪武至天順年間至少有十一次正式遣使帖木兒。帖木兒的使者每次入京,都采購大批絲織品。從帖木兒輸入中國的商品,有馬、獅子、鸚鵡、玉石等。就明朝而言,除了馬之外,其他物品并無多少經(jīng)濟(jì)效益,對此明朝負(fù)責(zé)接待的官員略有不滿。成祖認(rèn)為,兩國之間的交往,并不僅僅為了物質(zhì)利益,應(yīng)該從政治利益考慮。明成祖愿意與中亞等建立沒有經(jīng)濟(jì)利益或者經(jīng)濟(jì)收益甚微的國家政治關(guān)系,是一種深謀遠(yuǎn)慮的政治策略[14]。太祖成祖兩代為了表示對帖木兒帝國的重視,特令河西走廊一帶的地方官員將帖木兒帝國使節(jié)護(hù)送到京城,對流落在河西地區(qū)的中亞商人,凡愿回國的,資助其路費并負(fù)責(zé)護(hù)送回國。明朝還發(fā)展到帖木兒帝國的驛站。從中原到中亞,沿途“使站驛相通,道路無壅,遠(yuǎn)國之人,咸得其濟(jì)”[15]。
五、派遣使者傅安、陳誠出訪西域中亞,延續(xù)西域中亞文化交流傳統(tǒng)
繼承歷史傳統(tǒng),向絲綢之路西域中亞段沿線地方政權(quán)和國家派遣使者,建立貢使關(guān)系,是太祖成祖兩代經(jīng)略絲綢之路的又一項舉措。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太祖派傅安、郭驥等攜帶信函珍寶,率領(lǐng)一千五百人的使團(tuán)前往中亞帖木兒,這是明太祖第一次向中亞派出使者。傅安(?—1429),字志道,祥符(今河南開封)人。明初歷任四夷館通事等職。四夷館是明朝中央政府專事翻譯邊疆民族和鄰國語言文字的機(jī)構(gòu),鴻臚寺是負(fù)責(zé)外交禮儀的部門,傅安在這兩處任職多年,知曉外族語言和風(fēng)俗習(xí)慣,這是其出使西域中亞的有利條件。傅安一行由肅州出玉門關(guān),經(jīng)哈密、吐魯番、別失八里(今伊寧市),穿伊犁河谷到達(dá)撒馬兒罕。此時,中亞帖木兒西征初勝,力威氣盛,對明朝“驕倨不順命”,利誘傅安一行投降。為了籠絡(luò)傅安一行,派臣下帶領(lǐng)傅安一行巡視帖木兒帝國,先后到達(dá)今天伊朗的大不里士、伊斯法罕以及阿富汗的赫拉特,炫耀帝國功績。遠(yuǎn)道而來的明朝使團(tuán)面對帖木兒的誘降,表現(xiàn)出高度的民族氣節(jié)。心懷異志的帖木兒將傅安一行扣留下來。永樂三年(1405年)帖木兒去世后,永樂五年(1407年)六月,帖木兒新王沙哈魯派遣使者虎歹達(dá)等送傅安回國,此時傅安出使中亞離開故鄉(xiāng)已經(jīng)十三年了。明代陳繼儒《見聞錄》云:“初安之使西域也,方壯齡,比歸,須眉盡白,同行御史姚臣、太監(jiān)劉惟俱物故,官軍千五百人,而生還者十有七人而已。”傅安返明后,向明成祖匯報了赴帖木兒帝國及西域中亞所見所聞。永樂六年(1408年)四月到永樂七年(1409年)六月,傅安征塵未洗,再次奉命護(hù)送前來通貢使者返回,出使西域中亞,并頒賜沿途其他諸國。及至返回時,“撒馬兒罕、哈烈、火州諸國隨安等入朝,貢西馬五百五十匹”。此后西域地方政權(quán)和中亞諸國“……或比年,或間一歲,或三歲,輒入貢”。以后傅安又在永樂九年十二月至永樂十一年十一月、永樂十二年十月、永樂十四年三月出使西域和中亞。傅安先后六次出使西域中亞地區(qū),足跡遍布西域中亞各地。傅安的出使,促進(jìn)了明朝與西域中亞各民族的互相了解和信任,為絲綢之路商路暢通作出了積極貢獻(xiàn)。由于史料記載缺失,不知何故,傅安最后一次出使西域中亞又滯留九年,直到洪熙元年(1425年)七月才返回。傅安出使三十年后,明左春坊大學(xué)士曾榮為傅安匯編的《西游勝覽》序中談及傅安出使之壯舉:“洪武中,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jìn)貢馬駝騾衣甲之屬,禮意甚恭,既而西北諸巷往往傾向中國,欲盡事大之誠而弗可得。蓋當(dāng)其時,太祖皇帝方大施恩信以懷遠(yuǎn)人。使其知所感慕,乃遺禮利給事中傅安往使其固,以通道,且修報施之禮焉。”從中可以看出,太祖成祖在處理與中亞關(guān)系方面基本奉行歷代中原王朝遠(yuǎn)懷近柔的政治理念,以此擴(kuò)大影響。明太祖在派遣傅安出使西域中亞的同時,又派遣陳誠出使西域中亞。陳誠(1365—1457),江西臨川人。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因撒里畏兀兒事急,番邦酋長請求明出使洽談,太祖在儒臣中選拔能文能武者,出使西域,左右大臣力薦陳誠。陳誠欣然從命,于三月二十四日率使團(tuán)持節(jié)遠(yuǎn)行。陳誠一到西域,安撫各番,化解各番邦糾紛,重新設(shè)置安定、阿端、曲先三衛(wèi)。此后明朝對各衛(wèi)正式實施管轄權(quán)。明成祖繼位后,于永樂十一年(1413年)派遣陳誠與中宮李達(dá)等與哈烈和撒馬兒罕使者一同回訪答謝并處理朝廷與西域中亞諸國相關(guān)事宜,并送璽書、文綺、彩幣、布吊、瓷器、茶葉,以示安撫親善之意。他們于八月初一從北京出發(fā),首站哈密,依次出訪魯陳城、火州、鹽澤城、崖兒城、吐魯番、于闐、別失八里、養(yǎng)夷、渴石、卜花兒、達(dá)什干、賽蘭城、沙魯海牙、迭失迷城、撒馬兒罕,終站哈烈,共十七國。歷時三載,行程三萬里。永樂十三年(1415年)冬返回北京。陳誠將沿途所見記錄下來,撰寫成《西域行程記》和《西域番國志》,前者為西使的日程記錄,后者記載所歷各地山川地貌、風(fēng)俗人情,進(jìn)呈成祖。陳誠《西域行程記》詳細(xì)記載出使路線,為以后東西交通發(fā)展,積累了經(jīng)驗。之后,哈烈、撒馬兒罕、別失八里、失剌思、俺的干、俺都淮、吐魯番、火州、柳城和哈實哈兒等西域地方政權(quán)和中亞國家,遣使朝貢和派龐大的經(jīng)貿(mào)代表團(tuán)到明朝,最多的時候,哈烈、撒馬兒罕、別失八里等國的使團(tuán)多達(dá)三百人。永樂十四年(1416年)四月陳誠一行又出使西域中亞,十六年(1418年)四月返北京。永樂十六年十月,明成祖又派陳誠和中官郭敬出使西域中亞,陳誠又一次抵撒馬兒罕、哈烈,十八年十一月返北京。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四月,成祖再次派陳誠出使西域中亞諸國。五月,使團(tuán)將出塞,九月成祖病逝。仁宗即皇帝位,他不務(wù)遠(yuǎn)略,召西域使臣還京。陳誠等于十一月回到北京,此次出使中途而廢。陳誠自洪武二十九年至永樂二十二年,在前后二十九年的外交活動中,先后五次往返西域中亞諸國,遍歷諸國,宣傳明朝對外政策,與所到之處建立了友好關(guān)系。在永樂年間,撒馬兒罕和哈烈赴明朝使團(tuán)有二十二個,中亞其他城鎮(zhèn)使團(tuán)有三十三個,西域哈密等地有使團(tuán)四十四個。從明太祖到成祖時期,派遣傅安、陳誠出使西域中亞,對加強(qiáng)明朝與西域中亞的聯(lián)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也為促進(jìn)絲綢之路暢通,東西方經(jīng)濟(jì)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貢獻(xiàn)。傅安、陳誠等使者奔波往來于西域古道沙海綠洲,歷時近三十年,為睦鄰友好,溝通文化,發(fā)展貿(mào)易,鞏固邊疆,作出了巨大貢獻(xiàn)。
六、結(jié)語
從明太祖成祖經(jīng)略絲綢之路的一系列措施可以看出,明朝建立后深知絲綢之路的重要性,十分重視對絲綢之路的經(jīng)略,但是由于蒙古后裔政權(quán)繼續(xù)活躍在西域中亞絲綢之路沿線,其經(jīng)略絲綢之路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和障礙。明朝西域中亞歷史發(fā)生著深刻的變革,絲綢之路局勢與漢唐大為不同,一是這一時期人口密度和民族成分較之漢唐時期更復(fù)雜更多元,文化形態(tài)也更豐富,這里不僅有佛教文化,還有伊斯蘭教文化,使明代經(jīng)略此地困難重重。二是明朝與蒙元的特殊關(guān)系,使明朝不得不加強(qiáng)對蒙古的防御,面對蒙元后裔繼續(xù)活動的絲綢之路,明朝處于兩難境地。一方面要防范蒙古部族政權(quán)的興起,另一方面要加強(qiáng)和西域中亞的聯(lián)系。明朝試圖利用受伊斯蘭教教化的突厥人和蒙古部族勢力遏制北方和新疆北疆蒙古瓦剌等部,扶持在絲綢之路上傳播正酣的伊斯蘭教勢力,積極與西域中亞各地方政權(quán)建立聯(lián)系,牽制蒙古部族勢力的復(fù)興。在北部草原絲綢之路,明朝采取嚴(yán)密防守辦法,設(shè)關(guān)置隘,重兵把守。這些策略客觀上加強(qiáng)了與西域中亞絲綢之路沿線政權(quán)和國家的關(guān)系,有利于伊斯蘭教的傳播,促進(jìn)了我國穆斯林民族共同體的形成。這是明朝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特點。按照明代面臨局勢來看,太祖成祖經(jīng)略絲綢之路還是比較成功的,保證了和西域中亞的友好交往和商貿(mào)流通,遏制了蒙古瓦剌部落南下,防范了他們在這一地區(qū)的興起,維護(hù)了國家安定。明太祖成祖父子兩代深謀遠(yuǎn)略探索與西域中亞的交往,其謀略絲毫不遜于漢武帝和唐太宗,只是其面臨的形勢已經(jīng)發(fā)生變化,非個人力量能夠輕易改變,學(xué)術(shù)界應(yīng)對此給予公正評價。
作者:鄧慧君 單位:甘肅省社會科學(xué)院 政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