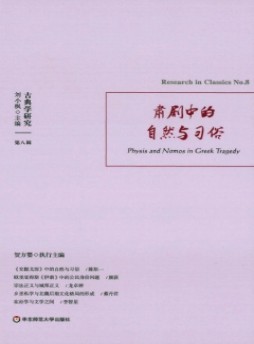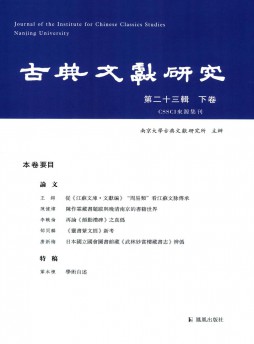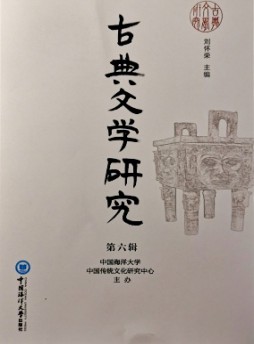古典詩詞中的生態文化映像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古典詩詞中的生態文化映像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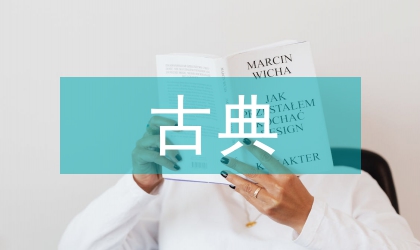
對于人類來說,生態環境既是物質家園,也是精神家園。人們對生態環境,不僅局限于物質層面和基于實用目的,而且通過心靈去感知,產生美丑、喜憂、好惡等不同的感覺,并通過各種文學藝術形式加以表現。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生態思想多半是直覺的、感悟的、混沌的、靈性的表述,古代科學記載中很少涉及生態環境的變遷。正史除了《災異志》和《地理志》之外,很少涉及現代意義上的環境變遷。相反,詩歌中的相關內容卻非常豐富。詩歌對山川、河流、動物、植物、氣候、物侯乃至許多重要環境事件的大量記誦,是我們用以勾畫不同時期環境歷史面貌所必須依憑的材料。利用詩歌材料,探討某地生態環境及其變化,進而推測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的協同變化過程,是很有意義的。清代詩人李調元說:“自古詩人例到蜀”。歷史上,許多大詩人都曾宦游、寓居成都,他們不僅留下大量膾炙人口的作品,而且也把成都溫潤秀美的自然環境、悠閑安逸的人文氣息描繪入詩。只是這類材料需要認真甄別,了其虛實,因為文學藝術對于自然現象、生態環境的記述,不僅有寫實、白描,也有簡化、夸張和想象。本文試從生態環境的角度,以古詩詞為基本史料,對歷史上的成都生態環境進行考察。
一、空氣清新,天青無塵
唐朝詩人李白毫不掩飾自己對成都的夸贊“,水綠天青不起塵,風光和暖勝三秦”(《上皇西巡南京歌》其九)。事實上,由于地處盆地,成都多云霧,尤其是冬天,不像高原地區,藍天白云,高遠遼闊。盡管如此,那時成都的天空卻是非常潔凈,沒有灰塵,沒有霧霾,空氣十分清新。作為一個外鄉人,南宋詩人陸游同樣贊不絕口:“劍南山水盡清暉,濯錦江邊天下稀”(《成都書事》),意思是,蜀中山明水凈,風光秀美,成都更是天下少見。清初詩人王士禛初到成都時,正值秋天,依然是山青水秀,竹木蒼翠,空氣清新純凈“。南過蠶叢國,秋風正授衣。青山初日上,黃葉半江飛。修竹連千畝,高楠徑十圍。臨江呼渡舸,極目一清暉。”(《新津縣渡江》)杜甫對唐代成都優良空氣的間接描寫,則更直觀更形象,也更為人熟知。“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絕句》)詩人在家中,憑窗而望,雪山近在眼前。如果空氣能見度不是非常好,一百公里外的景物是根本不可能看到的。在其他詩中,杜甫也描寫過西邊的雪峰,如在草堂早起望見“西嶺紆村北”(《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之十一),在浣花溪上劃船,目睹“練練峰上雪”(《泛溪》),出城時抬頭看見“斜景雪峰西”(《出郭》)。
一般來說,成都看見雪山幾率最高的時候是在5—6月、9—10月,這兩段時間內市區霧氣不重,海拔4000米以上山峰都有積雪。即使沒有雪山,也能看到群山青翠秀麗的景象。唐代詩人段文昌所見即是,“重樓窗戶開,四望斂煙埃。遠岫林端出,清波城下回。乍疑蟬韻促,稍覺雪風來”(《晚夏登張儀樓呈院中諸公》)。他站在城內張儀樓上,遠處青山不但躍入眼簾,而且似乎覺得有雪風隱隱而來。宋朝詩人吳中復說“:信美他鄉地,登臨有故樓。清風破大暑,明月轉高秋。朝暮岷山秀,東西錦水流。賓朋逢好景,把酒為遲留”(《西樓》)。他又在《西園十詠詩序》中說:“成都西園,樓榭亭池庵洞,最勝者凡十所。其間勝絕者,西樓賞皓月,眺岷山。”賞明月,觀遠山,都說明空氣潔凈,能見度好。今天的成都,高樓林立,污染加重,人們在市區幾乎是看不到山的。但如果雨過天晴,能見度好,站在高樓上西望,還是能看到群山連綿、雪峰聳立的景象。據專家考證,能夠看見的雪山包括四姑娘山的幺妹峰、龍門山一帶的西嶺雪山,以及南邊雅安方向的一些雪山。只是,這樣的機率已大不如昔了。
二、河渠縱橫,綠水長流
成都地區多淺丘平原,降水豐沛。岷江自崇山峻嶺中一路急流而下,到灌縣地域后進入平川地界,洪水季節常常泛濫成災。戰國時期蜀守李冰建都江堰,將岷江水分流。經過不同歷史時期的開河筑渠,從都江堰到成都東邊的龍泉山脈,數十條大小河流從西北向東南流向成都平原,形成了以南河、府河、沙河為干流環抱成都、并有上百條支流穿行城中的河網。城市格局也從秦漢魏晉的“二江珥市”,到唐宋時期的“二江抱城”,直至近現代的“江環城中”,正像李白說的那樣“,芳草籠秦棧,春流繞蜀城”(《送友人人蜀》)。傅崇矩(1875-1917)在《成都通覽》一書中說:“四川雖蜀山國,而成都實為澤國,因江河貫通,水利溥及也。”歷史上,與環城二江相通的有金河、御河,流經城內;與江河相連的有摩訶池、上下蓮池、江瀆池等,遍布城內外。這種河池眾多、綠水長流的江城特色,正如五代十國時期女詞人花蕊夫人描述的那樣,“長似江南好春景,畫船來往碧波中”(花蕊夫人《宮詞百首》之一)。所謂“二江抱城”,是指府河、南河環抱成都,此二江合稱錦江。很多詩人都曾吟詠過錦江,相關詩詞多達千余首。如李白“錦水東流繞錦城”(《上皇西巡南京歌》其七),杜甫“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云變古今”(《登樓》)。唐代詩人張籍“行盡青山到益州,錦城樓下二江流”(《送客游蜀》),則道出了一個初入蜀的外鄉人對成都這種江城景色的清新感受。他在《成都曲》中進一步描述說“: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萬里橋邊多酒家,游人愛向誰家宿?”順著錦江西望,新雨初霽,在綠水煙波的背景下,山頭坡前,荔枝垂紅,四野飄滿清香;而從萬里橋到浣花溪,沿河酒家密布,一派田園閑適風光。
唐代的錦江不僅風景絕美,而且能夠通航。都江堰至成都可以放筏、漂木、行舟,成都自錦江以下則可通大船。“濯錦清江萬里流,云帆龍舸下揚州”(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杜甫《絕句四首》),便是當時成都水路交通的真實寫照。這與岑參“成都與維揚,相去萬里地。滄江東流急,帆去如鳥翅”(《萬里橋》)描寫的情況相一致。由此可見,那時的錦江江面寬闊,水量很大。當岷山化雪、錦江漲潮時,清人沈廉看到了這樣壯闊的景象“:桃花落盡春水生,錦水忽作輥雷鳴。奔流欲轉草堂去,大聲撼動芙蓉城。”(《錦江觀潮》)自岷山而來的錦江,水質優良,江水清澄。從不同時期的詩作中可見一斑,如唐代崔備“遙連雪山凈,迥入錦江流”《和武相公中秋錦樓玩月得前字、秋字二篇》,唐代劉兼“煙雨樓臺漸晦冥,錦江澄碧浪花平”(《登郡樓書懷》),宋代黃庭堅“西瞻岷山兮東望峨眉,錦江清且漣漪”(《送焦浚明》),清代印愚“野店臨江石級斜,炊煙簇簇裹稠花。偶然小坐渾忘去,旋汲清流為點茶”(《府江棹歌》)。直到近代以至20世紀五六十年代,錦江之水還有以飲用、釀酒,如傅崇矩在《成都通覽》中說:“成都之水,可供飲料者,以河水為佳,因源流來自灌縣內之雪山也。”江水還被用來濯錦,錦江得名即與此有關。譙周《益州志》載:“成都織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勝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唐高駢“蜀江波影碧悠悠,四望煙花匝郡樓。不會人家多少錦,春來盡掛樹梢頭”(《錦城寫望》)。碧水長流,自然少不了魚蝦出沒。如杜甫“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陸游“易求合浦千斛珠,難覓錦江雙鯉魚”(《成都行》),清尉方山“錦里名花開炯炯,花光掩映秋光冷。漁舟一葉蕩煙來,劃破錦江三尺錦”(《錦江絕句》)。清澈的流水和波光滟瀲的湖池,給城市帶來靈氣。長期以來,成都市民形成親水、樂水傳統,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游賞習俗。一汪碧水的摩訶池、江瀆池、龍躍池,沿城而流的錦江,穿城而過的解玉溪和西郊的浣花溪,因錦江而興的西園、西樓,都是成都官民、文人游賞的最佳去處。唐宋時期歲時節令,沿著解玉溪—錦江—浣花溪一線舉行的水上遨游,是成都人的文化盛事。
三、花木繁盛,四季常青
成都一馬平川,土地肥沃,冬無嚴寒,夏無酷暑,雨量充足,溫潤宜人,適合多種花木生長。尤其是對于見慣了冬季萬物凋零、草木蕭索的北方人,成都冬天的蒼綠更讓人贊嘆不已,杜甫就曾寫道“: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成都府》)從唐宋詩詞可以看出,成都城內綠樹成蔭,四季花開“,綠樹成帷連藥市”(陸游《馬上》),栽種的樹木主要有槐、柳、楊、竹、松、柏、楠等。槐樹易于栽培,枝葉蔭濃,在唐宋成都城內街道兩旁種植較為普遍。陸游詩中描述較多,如“溝水浸新月,街槐生碧煙”(《七月八日馬上作》),“歸途細踏槐陰月,家在花行更向西”(《天中節前三日大圣慈寺華嚴閣燃燈甚盛游人過於元夕》)。在道旁、水邊,尤其是錦江兩岸,柳樹隨處可見。很多詩人都有過描繪,如:“拾遺被酒行歌處,野梅官柳西郊路”(蘇軾《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將老焉》),“遠柳新晴暝紫煙,小江吹凍舞清漣”(范成大《初三日出東郊碑樓院》)“,煙柳不遮樓角斷,風花時傍馬頭飛”(陸游《成都書事》),“獨詠滄浪古岸邊,牽風柳帶綠凝煙”(李新《錦江思》)“,曉出錦江邊,長橋柳帶煙”(陸游《曉過萬里橋》),“錦江橋畔白沙堤,楊柳千條夾岸低。最是晚煙橫練后,游人都愛出城西”(清•楊益濟《繁江竹枝詞》)。楊樹也是常見的一種行道樹。如“榆莢錢生樹,楊花玉糝街”(李白《春感》)“,楊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杜甫《田舍》)“,楊柳絲牽兩岸風”(花蕊夫人《宮詞》)“,迎馬綠楊爭拂帽,滿街丹荔不論錢”(陸游《江瀆池醉歸馬上作》)。此外,竹在河畔、宅第旁、園林中,也廣泛種植。范成大在《吳船錄》中記述成都郊外“家家有流水修竹,濃翠欲滴”,說“貪看修竹忘歸路,不管人間日暮寒”(范成大《綠萼梅》),杜甫“綠竹半含籜,新松才出墻……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香”(《嚴正公同詠竹》),陸游“青羊道士竹為家,也種玄都觀里花”(《青羊宮小飲贈道士》)。在寺觀祠廟中,則常種植松、柏、楠等,形成清幽的環境。如“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杜甫《蜀相》)“,楠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杜甫《高楠》)。
成都自古還享有“錦城花郭”的美譽,“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杜甫《春夜喜雨》)。梅花、海棠花、桃花、牡丹花、荷花、芙蓉花、菊花等,四季交替開放,正所謂“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蕊商量細細開”(《江畔獨步尋花七》其七),“城南十里盡栽花,翠翠紅紅處處遮。最愛路邊連理枝,愿教移植在農家”(《錦城竹枝詞》)。唐宋之時,成都的梅花甚為有名,從城西青羊宮到浣花溪一帶梅樹成林,花開時節,香溢數里。杜甫云“: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西郊》),陸游曰“:當年走馬錦城西,曾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斷,青羊宮到浣花溪”(《梅花絕句》)。陸游中年入蜀,在蜀中生活近八年,詠梅詩即多達三十余首。據陸詩記載,成都西、南、東門郊外梅花最盛,西郊以浣花溪、青羊宮一帶為主“,西郊梅花矜絕艷,走馬獨來看不厭”(《西郊尋梅》)。梅花開時,游人如織,盛況如陸游形容的那樣“:錦城梅花海,十里香不斷。醉帽插花歸,銀鞍萬人看”(《梅花絕句》其二)“,江郊車馬滿斜暉,爭趁城南未闔扉。要識梅花無盡藏,人人襟袖帶香歸”(《看梅歸馬上戲作》其五),足見當時梅花之繁盛。成都古代又稱海棠國,陸游贊道“成都海棠十萬株,繁華盛麗天下無”(《成都行》)。“濯錦江頭幾萬枝”(唐•賈島《海棠》),數以萬計的海棠花爭相怒發,花香彌漫、嬌艷芬芳,其壯觀可想而知。“云綻霞鋪錦水頭,占春顏色最風流。若教更近天街種,馬上多逢醉五侯”(唐•吳融《海棠》),錦江兩岸,海棠花開,如云綻霞鋪,占盡風流,如果把這些海棠移植到長安,那些官員們都要如癡如醉。宋朝詩人梅堯臣說“:蜀州海棠勝兩川,使君欲賞意已猶。春露洗開千萬株,燕脂點素攢細梗。朝看不足暮秉燭,何暇更尋桃與杏。”故而,時人皆稱“錦城海棠妙無比”(宋•汪元量《錦城春暮海棠花》),也難怪陸游在詩中要高歌“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氣可壓千林”了(《海棠》)。
今天,芙蓉花是成都的市花。五代十國時,后蜀皇帝孟昶偏愛芙蓉花,命百姓在城墻上遍植,秋天花開時節,成都“四十里為錦繡”,孟昶曾對身邊的人說:“自古以蜀為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五代詩語》卷四)。故成都又被稱為芙蓉城,簡稱“蓉城”。后蜀張立詩云“:四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下照坤維”《詠蜀都城上芙蓉花》,生動地描繪了滿城遍布芙蓉花的景觀。成都綠樹成蔭,繁花似錦,園林如畫,正如李白贊頌的那樣“,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草樹云山如錦繡,秦川得及此間無”(《上皇西巡南京歌》其二)。也無怪乎千百年來,詩人們吟詠不已。
四、田園如畫,生態宜居
成都沃野千里,自古被稱為“天府之國”。早在秦漢時期,成都就“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漢書•地理志》)。左思《蜀都賦》稱成都平原“: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其園則林檎枇杷,橙柿梬楟。榹桃函列,梅李羅生。百果甲宅,異色同榮”。宋人范成大《吳船錄》記述其在成都所見“,家家有流水修竹……濃翠欲滴”“,流渠湯湯,聲震田野,新秧勃然郁茂,美田彌望”“,綠野平林,煙水清遠,極似江南”。從飛機上鳥瞰,成都平原上星羅棋布著許多大大小小的翠綠色塊,這便是獨具特色的川西林盤。林盤是由農家院落與周邊的竹林樹木以及外圍的耕地、河流等形成的有機生態體,它是成都平原田園風貌的典型畫面。成都的林盤多數是竹子、喬木等構成的混合林帶“,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杜甫《江畔獨步尋花》其三)形象地展示了人們伴竹臨水散居的特點。成都溫潤的氣候、優美的環境、安逸的生活,歷來為文人鐘情并傳誦。杜甫的草堂生活便是一典型例證。杜甫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建草堂居住時間近四年,主要創作于成都及其周邊并留傳下來的詩篇約二百七十多首。其中,最突出的是對成都生態宜居、田園風情的吟詠。“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這是杜甫開始卜居成都草堂時所作。當時,天下大亂,而錦里(即錦官城成都)不在煙火亂塵中。他所在的小村,流水淙淙,圓圓的小荷葉漂浮在水面上,小麥花輕輕飄落,靜謐而美好。杜甫棲居成都的日子,身心得到了暫時的放松。
在風和日麗的季節,他常捧一卷書,在楠陰棕影下吟一會詩,飲幾杯酒,下一局棋,傾聽風葉的低吟、燕子的絮語、黃鶯的和鳴;他時常漫步溪邊江畔,看出水的紅蓮、逐波的白鷗、出水的魚兒、翩飛的蝴蝶“。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客至》),“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絕句四首》之三),“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水檻遣心二首》)“,櫸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鸕鶿西日照,曬翅滿魚梁”(《田舍》)。詩人陶醉了,“江皋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漫成二首》其二)。不單杜甫所居如此,其左鄰右舍也呈現出美麗恬淡的村居風光。他在江畔散步,看見“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江畔獨步尋花》其七》其六)“,隔戶楊柳弱裊裊,恰似十五女兒腰”(《絕句漫興九首》其九)。他去鄰居家做客“,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南鄰》),看見主人園里種著芋頭,栗子也都熟了;兒童笑語相迎,臺階上啄食的鳥雀,見到人來也不驚飛;晚歸之時,小船劃動,秋水新月,白沙翠竹。這是一幅多么明凈、清幽、自在、和諧的畫面!以上這些,不但體現了成都的自然生態之美,也襯托出了詩人對這種幽居、閑適生活的滿足和享受。難怪詩人離開成都以后,仍然念念不忘,他吟詠道:“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嶺界天白,錦城曛日黃。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懷錦水居止二首》其二),足可看出詩人對這片土地的深深眷戀之情。宋朝詩人范成大以田園詩聞名,他筆下的成都,“約束南風徹夜忙,收云卷雨一川涼。漲江混混無聲綠,熟麥騷騷有意黃”《(四月十日出郊》),初夏云收雨霽,天地一派凈碧,新麥初黃。當秋夜初涼時“,江頭一尺稻花雨,窗外三更蕉葉風”《(新涼夜坐》)。成都美麗的田園風光被后來的的詩人繼續吟詠著“。放鵝水闊兒童喜,煮繭煙濃婦女忙。日夜筒車鳴軋軋,引泉何必羨江鄉”(清•王侃《田家》其四)“。西山隱隱在郊扉,野店溪橋入翠微。春草馬蹄兼蝶舉,夕陽牛背帶鴉歸。清渠激溜村舂急,古木寒花市火稀。賴有故人留我宿,一樽綠酒卸塵衣”(清•顧復初《同葉雪蓀郎中至犀浦》)。民國詩人易君左《偶成》“:細雨成都路,微塵護落花。據門撐古木,繞屋噪棲鴉。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承平風味足,楚客獨興嗟。”
五、結語
莊子在《齊物論》中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齊一。”人與萬物平等,相互依存,同生共存才能持續發展。我國古代許多詩詞作品都自覺不自覺地演繹著、表現著這種樸素的生態美意識,抒寫著人與自然物相互依存的美好關系,肯定著人的生態性存在和精神性存在的快樂與大自然的不可分離性。迄今,生態環境日益惡化,可持續發展是必要的戰略選擇。維護生態多樣性是構筑生態園林城市的重要目標之一。成都在現代城市規劃建設中,應充分保護和利用好山水資源,并將其作為城市綠色空間發展基本脈絡,盡量避免因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造成的破壞和影響。同時,既有的歷史文化需要得到保護,特別是成都特色的山水田園以及生產生活方式。加強對川西林盤保護,既是對生態的保護,也是對村莊村落的保護,對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保護,更是對歷史文化的保護。
作者:馮凌宇 單位:中共成都市委黨校學報編輯部
- 上一篇:伊斯蘭生態文化的啟示范文
- 下一篇: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文化初探范文
擴展閱讀
- 1古典文化
- 2古典詩吟唱
- 3古典文學
- 4古典詩歌語言特征
- 5古典時代雅典婚配模式
- 6古典詞學趣范疇承傳考察
- 7古典園林建筑在古典園林中的作用
- 8古典藝術風格
- 9古典經濟學
- 10古典詩吟唱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