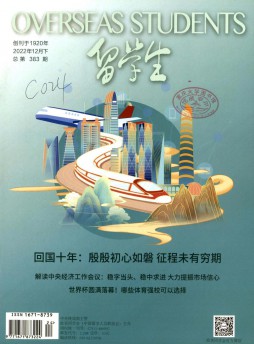留學熱潮與文學源流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留學熱潮與文學源流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留學運動,是在中國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興起的。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二次出國留學熱潮,主要是在日本留學。自1896年清廷正式派遣赴日留學人員到1906年,中國留日學生人數從13人急劇增加到8000多人。1908年7月,早稻田大學清國學生部教務主任青柳篤恒在師范本科第一屆畢業典禮的學務報告上指出:“有謂留學日本之清國學生,一時多達一萬三四千……其實最高人數僅達八千矣……”[1]38據統計,1902年,中國留日學生數為573人,1903年有1300多人,1904年留日人數為2406人,1905年至1906年人數猛增到8000多人。由此可以看出,近代留日學生是較早且較成規模的汲取西學的留學生群體。他們負笈東洋,或因“求強求富”的官方立場,或因救亡圖存、改革國政的使命感,或因變革思想、開啟民智的知識分子責任感等,在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都做出卓越的貢獻。相對于文化教育領域來說,留日學生東渡主要目的更多強調獵取功名,借革命思想和激情來排解心中諸多不滿,即使在教育領域,也多致力于學習政法和軍事學科。梁啟超1902年在流亡日本時寫道:“所學者,政法也,法律也,經濟也,武備也,此其最著者也。”[2]然而,在文化領域學習者人數也是比較多的。1903年,駐日公館兼留學生監督楊樞向清政府報告:“現查得各學校共有中國學生一千三百余人,其中學文科者一千一百余人,學武科者二百余人。”[3]并且在近代文化教育建設方面,大量的留日學生所作出的貢獻和影響巨大。可以說,中國的新教育和新文學的發展從一開始到以后之有驚人發展,直接或間接和留日學生有關。這些留日先驅者歸國后,把日本教育制度和教育中所汲取的思想移植到我國。1902年我國首次制訂的近代學制(壬寅學制)和1903年第一次實行的近代學制(癸卯學制)即是來源于日本。20世紀初,中國剛興學堂,創設新式學校時,教員中大部分是在留學日本政策下,到日本受速成教育回來的,或是由受聘到中國的日本教習所教導出。在文學方面,涌現出了一大批在中國新文學運動中成為新文學觀念的倡導者和文學革命的闖將。因而中國新文學的發生與留日教育是密切相關的,變革思想與開啟民智是教育與思想發生關系的一個主要表現作用。中國新文學的主要人物,不論是以魯迅為代表的語派,還是以郭沫若為代表的創造社,幾乎全是留日學生。雖然時間上有先后,但是在文化汲取上卻是承上啟下的。周樹人、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說集》,不但在日本編纂,而且在日本出版。創造社也是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等人在留日期間成立的。他們最先發刊的是日文期刊《Gree》,不久就發展成了《創造季刊》、《創造月刊》、《創造周刊》和《創造日》并積極開展了一系列的文學活動。郭沫若也曾說:“中國的新文藝深受了日本的洗禮。”[4]費正清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強調:“20世紀的最初10年中,中國學生前往日本留學的活動很可能是到此前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出洋運動。”“在規模深度和影響,中國留日遠遠超過了中國學生留學其他國家。”他斷言:“從1898年到1914年這段時期,人們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重大影響。”[5]著名日本史研究專家汪向榮也認為:“不論怎么說,20世紀以后中國的歷史是和留日教育息息相關,有不可分割的關系。”[6]
近現代大規模的留學日本熱潮打破了文化教育上的封閉狀況,促成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通過從日本輸入的西學,中國移植了先進文化和先進教育思想并促進了國內文學思想的變革和發展。留日學生學習的內容,大多以“普通學”和“憲政”為主,但要實現憲政,必先普及教育。1898年8月20日在《太陽》第4卷第17號雜志刊載了文化教育部專門學務局長兼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上田萬年的《關于中國留學生》文章。文中論述了留學生來日本留學的意義及提出一系列建議,其主要旨趣強調“必須灌輸留學生以改革教育之精神,只有教育才是改革的根本”[1]25。雖然日本政府對待來日留學生的用心昭然若揭,但在客觀上卻促使了這些留學生得到了較完善的教育。上田氏還主張必須獎勵留學生兼修英語,以便通曉世界文明的真相。這就為留學生創造了較好的學習環境和寬泛的學習視野。留日學生外受新思想的啟發,內憂國勢危迫,他們在學習之余編輯出版發行各種期刊,以灌輸新思想、新知識于國內為己任。從教育思想上來看,變革思想與開啟民智成為留日學生自覺或不自覺的歷史承擔。這就決定了這些留日學生的任務不僅僅是排遣個人不滿情緒,更重要的是為復興本國文化尋找到一種新的出路。其中,翻譯日文西書成為吸收西方文明和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張之洞《勸學篇•廣譯》中指出:“各西學書之要者,日本皆以譯之,我取經于東洋,力省效速。……譯西書不如譯東書。”①康有為于1887年編成《日本書目志》,在序文中說道,“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人已略譯之矣”,因此翻譯日本書就是“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費不千萬金而要書畢集矣”②。但是,這一時期中國對日本文學的翻譯,具有“濃厚的急功近利的色彩”[7]。在大多數翻譯家看來,文學翻譯只是一種經世濟民、開發民智或政治改良的手段。他們看中的不是文學本身的價值,而是文學所具有的功用價值。在這種觀念的指導下,翻譯選題基本上不優先考慮文學價值,而是考慮其實用性。一方面宣揚維新政治,啟發國民的政治意識而大量翻譯日本的政治小說;一方面開發民智,向國民宣傳近代西方的科學知識、近代法律、司法制度、近代教育、軍事而大量翻譯日本的科學小說、偵探小說、冒險小說、軍事小說等。如日本近代文學的開山之作、二葉亭四迷的長篇小說《浮云》(1887-1890)反映的是處在近代官僚制度壓抑下的個人的苦惱和個性意識的覺醒,批判了當時的西化風氣,而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所拼命鼓吹的,卻是如何培養個人的國家觀念,如何引進西方文化。盡管留學生注重的是宣揚革命和改革國政的內容,但是新文學觀念正是蘊涵在這些狂飆突進的思想革命中。正如陳子展在《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中認為:“《新青年》最初只是主張思想革命的雜志,后來因主張思想革命的緣故,也就不得不同時主張文學革命。因為文學本來是合文字思想兩大要素而成;要反對舊思想,就不得不反對寄托舊思想的舊文學。所以由思想革命引起文學革命。”
思想革命引起文學革命,這是新文學得以發生的基本前提,也是文學觀念轉變的客觀條件。除了嚴復、胡適等一部分留學歐美的學者外,還有一部分來自于留學日本的黃遵憲、梁啟超、魯迅和陳獨秀。在近代中國急遽變化的現實面前,乾嘉以來的尊經與經世并重的文學觀念顯然包含著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因而,探討救世之道和尋求新的文學表現形式,就成為中國近代文學變革的基本內容。“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等口號,顯然是“大變”論的發展。文學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進行維新與革命斗爭的武器,因此激起文學領域中的廣泛“革命”。這些留學生承受近代進步思潮的鼓蕩,成為時代的弄潮兒,以富有時代氣息的創作打破傳統文壇的沉悶,與擬古的作家群形成對比。他們往往首先不是以作家而是以政治家、思想家的身份活動于近代歷史舞臺上,但他們卻以內容新穎的創作,成為領一時風騷的人物。最引人注目的是“詩界革命”與“文界革命”取得的成果,使詩文創作面貌一新,將近代詩文的發展推向了高峰,并為新文學革命準備了某些條件。資產階級文化思想更新帶來的文學變革之一,是詩歌領域出現的“詩界革命”。鮮明提出“詩界革命”口號的是梁啟超,而早已反映出詩歌變革趨向并獲得創作成功,成為“詩界革命”旗幟的則是黃遵憲。他早年即經歷動亂,關心現實,主張通今達交以救時弊。從光緒三年(1877)到二十年(1894),他以外交官身份先后到過日本、英國、美國、新加坡等地。經過親自接觸資產階級文明和考察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經驗,他明確樹立起“中國必變從西法”(《己亥雜詩》第四十七首自注)的思想,并在新的文化思想激蕩下,開始詩歌創作的新探索。他深感古典詩歌“自古至今,而其變極盡矣”,再繼為難。但他深信“詩固無古今也”,“茍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而筆之于詩,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詩者在矣”(《與朗山論詩書》)。他沿著這條道路進行創造性的實踐,突破古詩的傳統天地,形成了足以自立、獨具特色的“新派詩”,被梁啟超譽為“獨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紀詩界中”(《飲冰室詩話》三二),成為“詩界革命”的巨匠和旗幟。伴隨資產階級文化思想啟蒙運動而逐漸展開的首先表現在文體改革上。黃遵憲在光緒十三年(1887)所撰的《日本國志》中提出言、文合一的主張:“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他期望文章能夠接近通行的口語,“明白暢曉,務期達意”,“適用于今,通行于俗”,使得“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這顯然是從日本明治維新的歷史經驗中,認識到近代性質的社會變革對民眾進行思想啟蒙的迫切性,才將眼光轉向語文改革的問題上來,樹立起改革文學語言和文體的鮮明觀念。正因為主要動力出于宣傳新思想,所以文體改革的范圍也基本局限于文章領域。資產階級改良派領袖人物之一的梁啟超說:“國惡乎強?民智,斯國強矣。民惡乎智?盡天下人而讀書、而識字,斯民智矣。”③裘廷梁說:“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話若。”
文體改革以改良民智為軸心,面向社會的近代傳媒報刊在這方面起了帶頭作用,它較早地沖破了士大夫雅文學的觀念,邁出了通俗化的步伐。陳榮袞曾發表題為《論報章宜改用淺說》的文章,呼吁報章文字的通俗化,要求“作報論者”,以“淺說”“輸入文明”,并明確提出:“大抵今日變法,以開民智為先,開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不改文言,則四萬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居于黑暗世界之中,是謂陸沉;若改文言,則四萬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嬉游于琉璃世界中,是謂不夜。”報章文字的通俗化,形成不同于傳統古文的報章文體,這是文體語言的一大變化。資產階級文化思想催化的又一文學變革是“文界革命”。梁啟超既是“文界革命”口號的提出者,又是新文體的成功創造者。他在前追隨康有為,大力宣傳變法維新思想;戊戌政變后,流亡國外,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等,更加熱情地宣傳資產階級文化思想,致力于開通民智的“新民”工作,這都促使他立意使文學成為思想啟蒙的工具,因此他成為詩文小說戲曲革命的全面倡導者。而就其創作實績來說,貢獻最為突出、影響最為廣遠則在“文界革命”方面。他所創造的“新文體”散文,以比較通俗而富有煽動力的文字運載新思想,使他成為“新思想界之陳涉”[9]。他的這種“開文章之新體,激民氣之暗潮”的文章也形成浩大的聲勢,震撼了當時的文壇。先前留學日本的魯迅于1906年回到東京后,廣泛閱讀西方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和文藝作品。當時章炳麟在東京主編《民報》,宣傳革命,并設班講授國學。魯迅因前往聽講,得識章炳麟,并加入蔡元培、章炳麟所創立的革命團體光復會。此時魯迅開始把喚醒人民的自覺,當作革命工作的中心工作,認為文藝是喚醒人民自覺的工具。他曾于1907年在留日學生的刊物《河南》上發表過四篇文章,其中《人之歷史》是介紹達爾文學說的重要論文,指出社會是發展的、進步的,將來必勝過去、青年必勝老年,為了鼓勵青年人向上,他甚至頌揚尼采的“超人說”。《文化偏至論》反對匆忙引進西方的物質文明和民主,認為中國人大多無知,在心理上還不能適應。這些文學觀念都成為新文學發生的主要思想源流。陳獨秀早年留學日本。其前期思想熱心于對文學進行“革命”,則是“意在沛公”。他在《文學革命論》中,除了抨擊古典文學的弊端,還使用了大量的諸如“革命”、“政治”、“國民”等社會化詞語。如“吾茍偷庸懦之國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雖經三次革命,而黑暗未曾稍減。”政治界的“三次革命”遭到失敗,在陳獨秀看來是因為“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柢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莫不黑幕層張,垢污深積,并此虎頭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單獨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會,不生若何變化,不收若何效果也,”因此他主張“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于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
對文學本身進行“革命”并不是陳獨秀的最終目的,他革新“文學”是為了改良政治,啟蒙、改造“庸懦之國民”。1917年《新青年》雜志(第一卷名《青年雜志》)創刊為開端,在宣傳新思潮、開展啟蒙運動的同時,已經注意到了文學革命的必要性。《新青年》創刊后不久,針對國內文壇狀況,陳獨秀就發表了《現代歐洲文藝史譚》等文,介紹西方近代文藝思潮從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浪漫主義)到寫實主義(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的演進過程,并在與張永言的通訊中明確表示了文學改革的愿望:“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今后當趨向寫實主義。文章以紀事為重,繪畫以寫生為重,庶足挽今日浮華頹敗之惡風。”[11]這一主張曾得到胡適等人的贊同。可見,汲取西學成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首要使命,留日教育促成新文學的發生是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