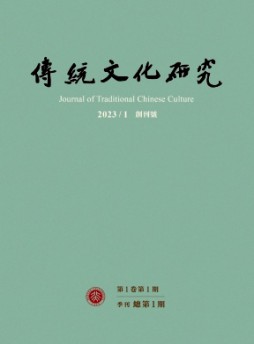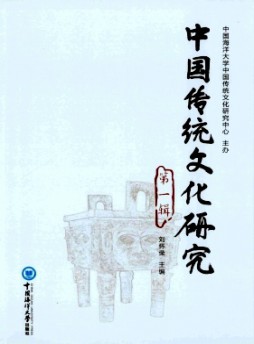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抉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抉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當(dāng)代美國(guó)印第安女作家路易斯·厄德里齊的《愛(ài)之藥》探討了回歸印第安文化傳統(tǒng)、追尋族裔文化身份的主題。厄德里齊在表述當(dāng)代印第安人回歸部族傳統(tǒng)的強(qiáng)烈愿望的同時(shí),通過(guò)小說(shuō)中的人物回歸傳統(tǒng)的失敗及向白人文化的妥協(xié),再現(xiàn)了《道斯法案》下保留區(qū)內(nèi)處于兩種文化夾縫中的印第安人的真實(shí)處境,也揭示出了印第安部族的未來(lái)生存之路,即在紛繁復(fù)雜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中,堅(jiān)守本部族的傳統(tǒng),維護(hù)本族裔的文化。
關(guān)鍵詞:《愛(ài)之藥》;印第安文化傳統(tǒng);文化身份
Abstract:InLoveMedicine,thethemeismainlytheculturalregressionandculturalidentityfortheNativeAmericansLouiseErdrichdepictedthelivingconditionsofaNativeAmericanReservationundertheimpactofDawesActandreflectedtheconflictsbetweenthetwokindsofcultures:traditionalNativeAmericancultureversusEuroAmericancultureShedemonstratedthefailureofculturalregressionandcompromiseonthecharactersinthenovelandstressedthattheonlywayfortheNativeAmericansistoprotecttheircultureandreturnbacktotheirtraditioninthemodernsociety,andthattheyhavetofightagainstthemarginalizationsoastosurviveinthewakeofculturalcatastrophe
Keywords:LoveMedicine;traditionalNativeAmericanculture;culturalidentity
自斯科特·莫馬迪(ScottMomaday)的《黎明之屋》(HouseMadeofDawn)在1969年獲普利策文學(xué)獎(jiǎng)以來(lái),印第安作家逐漸受到了美國(guó)公眾及白人主流文學(xué)的關(guān)注。此后的印第安文學(xué)蓬勃發(fā)展,涌現(xiàn)了一批優(yōu)秀的作家,如萊斯利·西爾科(LeslieMarmonSilko)、杰拉爾德·維茲諾(GeraldVizenor)、詹姆斯·威爾奇(JamesWelch)、路易斯·厄德里齊(LouiseErdrich)夫婦等。在《黎明之屋》發(fā)表之前,大多涉及印第安人的文學(xué)作品都是由非印第安族裔的作家所寫,他們筆下的印第安人是“野蠻的”、“未開(kāi)化的”,帶有這些作家對(duì)于印第安人的主觀認(rèn)識(shí),是不全面、不客觀的。在這樣的情形下,接受過(guò)良好教育的印第安作家們站了出來(lái),以文字的形式講述自己的故事及本部落的傳統(tǒng)文化,竭力在白人文化處于主流地位的社會(huì)中發(fā)出自己的聲音。他們?cè)谄渥髌分斜憩F(xiàn)的主題多為:土地對(duì)于個(gè)人乃至整個(gè)部族的意義;“家”的回歸及文化身份的追尋;保留區(qū)內(nèi)家族的衰落與重建;過(guò)去對(duì)現(xiàn)在(即傳統(tǒng)對(duì)現(xiàn)代)的影響;印第安傳統(tǒng)中的“講故事”和“治療”對(duì)印第安文化復(fù)興的作用等。這些主題在厄德里齊的小說(shuō)《愛(ài)之藥》中皆有體現(xiàn),她主張:只有回歸印第安傳統(tǒng)、了解印第安文化才是使當(dāng)代印第安人生存下去之根本。
厄德里齊于1954年出生在美國(guó)明尼蘇達(dá)州的小福爾斯鎮(zhèn)(LittleFalls),屬北達(dá)科他州龜山齊佩瓦族(Chippewa)人。厄德里齊并不是純種的印第安人,其父為德美混血,母親為印第安齊佩瓦族人,作為一個(gè)混血兒,她把自己的經(jīng)歷寫入了作品中。她通過(guò)作品中的人物講出自己的心聲,這些人物多以游離于白人世界的印第安人、混血兒為主,他們的故事與她的親身經(jīng)歷極為相似。她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小說(shuō)及詩(shī)歌,尤為著名的是四部曲:《痕跡》(Tracks,1988),《土著皇后》(TheBeetQueen,1986),《愛(ài)之藥》(LoveMedicine,1984),《賓格宮殿》(BingoPalace,1994)。四部小說(shuō)共同組成一個(gè)完整的故事,各部中的人物也相互聯(lián)系,講述了北達(dá)科他州印第安保留區(qū)內(nèi)幾代人的故事。這四部小說(shuō)的另一特點(diǎn)在于,每部作品都突出描繪自然界的一種元素,分別為水、空氣、土地和火,這些元素與印第安信奉的自然神相互照應(yīng)。
厄德里齊的第一部小說(shuō)《愛(ài)之藥》自出版以來(lái),受到評(píng)論界的極高贊譽(yù),獲得了許多獎(jiǎng)項(xiàng),并被選入大學(xué)的文學(xué)課程。1984年版的《愛(ài)之藥》由14個(gè)章節(jié)組成,1993年版擴(kuò)增至18個(gè)章節(jié),小說(shuō)的每一章都由一個(gè)人物來(lái)講述故事,各章故事的時(shí)間并不是連續(xù)的,小說(shuō)的第一章開(kāi)始于1981年,第二章的時(shí)間倒退到50年前的1934年,而后的章節(jié)按時(shí)間順序排列,一直到1984年。整部小說(shuō)涉及三代十多個(gè)人物,不同的人物講述家族歷史中的不同片斷,在他們各自的講述中也有著他們對(duì)共同經(jīng)歷事件的不同理解。這些小故事看似獨(dú)立,實(shí)則由一明一暗兩條線串連起來(lái):明線是家族中的第二代阿姨茹恩(June)的死,家族中的其他成員為參加她的葬禮從各處趕回家中,在彼此的交談和回憶中,填補(bǔ)了家族歷史的空缺;暗線是家族中的第一代祖母瑪麗(Marie)尋找“愛(ài)之藥”的過(guò)程,她希望借助“愛(ài)之藥”的力量重新獲得丈夫納科特(Nector)的愛(ài)。“愛(ài)之藥”是印第安古老神秘力量的體現(xiàn),是印第安文化傳統(tǒng)的延續(xù),因而厄德里齊選此作為全書的題目。本文從文化的傳統(tǒng)、文化沖突及文化選擇三個(gè)方面闡述當(dāng)代印第安人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所作出的抉擇,揭示印第安人回歸傳統(tǒng)、堅(jiān)守本族文化的重要意義。
一、文化的傳統(tǒng)
文化是一個(gè)抽象的概念,包括傳統(tǒng)、習(xí)俗、社會(huì)習(xí)慣、生活方式、思維模式、價(jià)值觀及世界觀等多方面內(nèi)容。印第安人以部族或群落的形式生活,每個(gè)部族或群落都有不同的文化,如在《愛(ài)之藥》中的人物是生活在印第安齊佩瓦族文化之中。印第安文化并不是一種單一的文化形式,而是由許多部族的文化共同構(gòu)成的文化體系。這些部族間的文化也有許多相似之處,如都受到地域的影響,都有相似的家族體系、有季節(jié)性的生活方式及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等,因而,廣義上的印第安文化即指以這些相似性為基礎(chǔ)的印第安文化體系。
自15世紀(jì)印第安人與白人的第一次接觸,印第安文化就受到了白人文化的影響,并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發(fā)生著改變。那么,當(dāng)代的印第安人又該怎樣追憶過(guò)去的傳統(tǒng)、尋找遺失的文化呢?印第安人是通過(guò)記憶了解本部族的歷史。由于歷史中存留著傳統(tǒng)文化的印跡,因而記憶是追尋印第安文化傳統(tǒng)的最有效途徑。記憶追溯歷史的主要表現(xiàn)是“講故事”,印第安的部落文化中自古就有“講故事”的傳統(tǒng)。整個(gè)家族聚在一起聽(tīng)長(zhǎng)輩講述本族的歷史、傳統(tǒng)儀式及神話傳說(shuō),故事世代相傳,在記憶中延續(xù)。整部《愛(ài)之藥》都是由不同的人物講述各自的故事、家族的故事和整個(gè)部落生死存亡的故事,并在回憶中勾畫出印第安的歷史及文化傳統(tǒng)。因?yàn)榛貞涍^(guò)去能夠使人進(jìn)一步了解自己的文化和歷史。過(guò)去是現(xiàn)在的基礎(chǔ),沒(méi)有歷史的積淀,就不會(huì)有現(xiàn)代的文化,而忽視傳統(tǒng)、否認(rèn)歷史不僅會(huì)喪失自我,還會(huì)迷失方向。正如語(yǔ)言心理學(xué)家大衛(wèi)·卡羅(DavidCarroll)曾說(shuō):“對(duì)于過(guò)去零碎的記憶及歷史片斷的回顧是很必要的。”[1]
既然記憶與傳統(tǒng)有著如此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倘若沒(méi)有了記憶,又會(huì)對(duì)文化產(chǎn)生怎樣的影響呢?《愛(ài)之藥》中的祖父納科特就是一個(gè)喪失記憶的人,從小接受過(guò)白人的教育,因?yàn)槌?887年頒布的《道斯法案》1887年美國(guó)政府頒布的《道斯法案》(DawesActorGeneralAllotmentAct)是針對(duì)“印第安問(wèn)題”而制定的印第安土地分配政策,采用同化的方式使印第安人融入美國(guó)社會(huì),通過(guò)分配土地的制度迫使印第安人成為“文明人”。《道斯法案》以法案制定人亨利·道斯(HenryDawes)的名字命名,他主張文明意味著穿戴文明的服飾、耕作土地、安居樂(lè)業(yè)、子女就學(xué)、喝威士忌酒并擁有財(cái)產(chǎn)。外,美國(guó)政府還采取了一系列輔助政策來(lái)加快同化印第安人的進(jìn)程,在印第安保留區(qū)內(nèi)修建了大量的教堂、學(xué)校,規(guī)定適齡印第安兒童入學(xué)接受教育。納科特成年后離開(kāi)保留區(qū),來(lái)到白人居住的小鎮(zhèn),希望在白人世界里找到屬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他做過(guò)好萊塢電影中的臨時(shí)演員,飾演的是蠻夷的印第安人形象,但影片中印第安人的結(jié)局多半是死亡或被白人征服。他還做過(guò)白人畫家的人體模特,畫家將畫定名為《勇者的跳水》,展現(xiàn)的是納科特赤身裸體跳入洶涌的河水中結(jié)束自己的生命。但根據(jù)齊佩瓦族的習(xí)俗,以溺水方式結(jié)束生命的印第安人的靈魂將不會(huì)輪回,只能變成在兩個(gè)世界之間徘徊的游魂。在經(jīng)歷了種種挫折后,他又重新回到保留區(qū)的家中,但他仍舊不能割斷與白人世界的聯(lián)系,依然能夠感受到白人文化的影響,生活在痛苦之中,終于在一場(chǎng)大火之后變得癡癡傻傻,失去了記憶。他的外孫女艾伯丁(Albertine)曾向他詢問(wèn)過(guò)去的事情,他總是搖著頭說(shuō):“我記得日期卻不記得發(fā)生過(guò)什么,記得住名字卻又記不起他們的面孔,即使能記起一些事情,卻又不記得究竟什么時(shí)候或在哪里發(fā)生過(guò)”[2]。記憶的喪失對(duì)納科特可算做一種保護(hù),使他免受過(guò)去痛苦往事的折磨。厄德里齊與丈夫于1990年接受電臺(tái)作者訪談時(shí)曾說(shuō):“對(duì)于納科特來(lái)說(shuō),他生命中發(fā)生的重大事件以及他心中的內(nèi)疚與自責(zé)都成為他精神與生活上的負(fù)擔(dān)。”他所擺脫的是在白人文化影響下的記憶,白人的文化和教育并沒(méi)有帶給印第安人文明和進(jìn)步,他們?cè)诎兹说难壑幸廊皇且靶U人的象征。忘記過(guò)去的痛苦、擺脫白人的束縛、重新回到印第安的文化與傳統(tǒng)是厄德里齊小說(shuō)中的主題。
納科特所代表的是當(dāng)代印第安人所面臨的困境,同時(shí)生活在白人與印第安兩種文化背景下,并在強(qiáng)勢(shì)的白人文化影響下,他忘記了本族的文化傳統(tǒng),在白人的世界中失去了身份,只能生活在社會(huì)的邊緣。印第安作家路易斯·歐文斯(LouisOwens)指出:“忘記過(guò)去就意味著喪失自我。”[3]失去記憶的納科特不僅生活上不能自理,還喪失了自我與身份。“忘記過(guò)去”可以理解為接受白人教育、受到白人文化影響的印第安人忘記了本部族的文化傳統(tǒng)和文化身份。這種“忘卻”或許并非出于自己的本意,而只是因?yàn)樗麄儾恢绾卧诎兹宋幕陀〉诎矀鹘y(tǒng)文化之間作出選擇。
二、文化的沖突
白人文化與印第安文化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如在宗教信仰及生活方式上,白人多信奉新教,印第安人信奉自然神;另一方面,白人文化強(qiáng)調(diào)個(gè)體的作用,在社會(huì)中組建“核心家庭”,印第安人注重群體,往往是部族的所有成員共同生活在一個(gè)大家族中。印第安文化重視對(duì)于智慧的認(rèn)知及意識(shí)的發(fā)展和追求,而白人文化重視對(duì)于信息的認(rèn)知及經(jīng)濟(jì)或物質(zhì)形式的追求。兩種文化的差異致使印第安人與白人接觸、溝通的不便,甚至?xí)斐蓛煞N文化的沖突。
自白人登上美洲大陸的那一刻起,印第安人就開(kāi)始了被殖民的生活。而后,白人在這塊新大陸上興建自己新的家園,不斷擴(kuò)大土地面積,并占有社會(huì)的絕大部分物資和財(cái)富。強(qiáng)勢(shì)的白人對(duì)印第安人實(shí)行邊緣化政策,排擠和壓制印第安的力量。1830年美國(guó)政府頒布的《印第安遷移法案》規(guī)定,美國(guó)東部的印第安人要全部遷往密西西比河以西為他們劃定的保留區(qū)內(nèi),實(shí)行種族隔離政策,這些“印第安保留區(qū)”絕大部分是偏僻貧瘠的山地或沙漠地帶。印第安人長(zhǎng)期遭到屠殺、圍攻、驅(qū)趕、被迫遷徙等迫害,人數(shù)急劇減少。在文化方面,印第安文化也處在弱勢(shì)的地位,白人文學(xué)一直處于美國(guó)文學(xué)的主導(dǎo)地位,這種狀況直到20世紀(jì)中后期才有所改進(jìn)。隨著民權(quán)運(yùn)動(dòng)的興起,一些印第安作家逐漸在美國(guó)文壇上發(fā)出自己的聲音。作為一個(gè)印第安女作家,厄德里齊深知在她面前的是一條不同于其他作家的路。她在1985年《紐約時(shí)報(bào)書評(píng)》上這樣闡述當(dāng)代印第安作家的任務(wù):“由于經(jīng)受過(guò)巨大的苦痛,他們指印第安作家。[ZW)]講述的必定是兩種文化沖撞中那些保護(hù)和弘揚(yáng)印第安文化的幸存者的故事。”[4]在厄德里齊的多部小說(shuō)中,確實(shí)體現(xiàn)出印第安文化與白人文化間的沖突,以及在此種社會(huì)環(huán)境下印第安人的困惑與掙扎,《愛(ài)之藥》也不例外。
小說(shuō)中印第安家族中的第三代子孫從小生活在保留區(qū)內(nèi),同時(shí)受到白人文化與印第安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艾伯丁的表弟利普沙(Lipsha)擁有印第安巫醫(yī)薩滿(Shaman)所賦予的神奇力量,通過(guò)“觸摸治療”(healingtouch)在保留區(qū)內(nèi)為人治病。祖母瑪麗希望借助他的神奇力量,尋找到印第安古老傳說(shuō)中的“愛(ài)之藥”,從而重新獲得丈夫納科特的愛(ài)。利普沙卻不知道該如何向印第安的神靈祈福,由于他自小受到保留區(qū)內(nèi)羅馬天主教的影響,便帶著制作“愛(ài)之藥”的材料雜貨店里買的兩顆生火雞心來(lái)到天主教堂。他懇求神父為兩顆火雞心賜福,卻遭到了拒絕,無(wú)奈之下,他只能安慰自己,憑借自己的力量也可以為之賜福,得到“愛(ài)之藥”。在兩種文化的背景下成長(zhǎng),利普沙不自覺(jué)地受到兩種文化的影響,也感受到兩種文化的沖突。他將“愛(ài)之藥”拿給瑪麗,告訴她只要她與納科特把兩顆生火雞心吃掉,他們的愛(ài)就會(huì)一直持續(xù)到永遠(yuǎn)。但納科特在吃下火雞心做成的“愛(ài)之藥”后卻窒息而死,瑪麗也因此失去了獲得丈夫愛(ài)的機(jī)會(huì)。不能說(shuō)文化沖突是致使納科特死亡的直接原因,但不可否認(rèn)的是,納科特的死是由火雞心制成的“愛(ài)之藥”造成的,而“愛(ài)之藥”的制作過(guò)程本身就體現(xiàn)著兩種文化的沖突。《愛(ài)之藥》并不是一部偵探推理小說(shuō),因此納科特的死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從尋找“愛(ài)之藥”的過(guò)程中所體現(xiàn)出的當(dāng)代印第安人面臨文化沖突的現(xiàn)狀。印第安人們有著自己的困惑和迷惘,他們不知道該如何在兩種文化中作出選擇:是堅(jiān)守古老的印第安文化傳統(tǒng),還是跟隨著居于主流地位的強(qiáng)勢(shì)白人文化;是追尋本部族的文化歷史、維護(hù)印第安的文化身份,還是接受白人文化的教化,以一種新的身份融入白人的世界?當(dāng)代的印第安人有著自己的選擇。
三、文化的選擇
文化的一大特點(diǎn)是具有地域性,生存在不同地域的人們所代表的文化是不同的。生活在保留區(qū)的美國(guó)印第安人受到兩種文化的影響,他們不知道該如何在兩種文化之間作出選擇,如何追尋文化身份。現(xiàn)如今,90%的印第安兒童是在非印第安文化的環(huán)境中成長(zhǎng),這也就導(dǎo)致了他們對(duì)文化身份的忽視,面對(duì)著白人文化對(duì)本族文化的壓制,他們?cè)谖幕臎_突中開(kāi)始了尋找身份之路。印第安作家TS索爾亞(Sawyer)對(duì)于身份的定義是:身份是一種概念,是一個(gè)族群在一個(gè)特定的生存環(huán)境中對(duì)所發(fā)生事件的思考方式,是對(duì)祖先的所作所為感到自豪的途徑,是區(qū)分不同族群的有效方式[5]。身份同文化一樣,也與土地之間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根據(jù)印第安的古老傳說(shuō),如果一個(gè)部落在一塊土地繁衍過(guò)幾代人,那么土地就具有了這個(gè)部落所賦予的生機(jī)和神奇的力量,展現(xiàn)著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的過(guò)去、現(xiàn)在和未來(lái)。
也正是因?yàn)槿伺c土地的關(guān)系是不可分割的,印第安人對(duì)于文化身份的追尋演變成對(duì)出生地的回歸“家”。“家”于印第安人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家”是印第安人聚集的保留區(qū),也象征著印第安的傳統(tǒng)文化。《愛(ài)之藥》中的許多人物在白人社會(huì)生活了一段時(shí)間后,又選擇回到保留區(qū)內(nèi),他們選擇了回家就是選擇追尋自己的文化身份、選擇回歸到印第安的傳統(tǒng)文化中。小說(shuō)的開(kāi)篇講述的是阿姨茹恩回家的過(guò)程,她在保留區(qū)內(nèi)長(zhǎng)大,成年后到白人居住的小鎮(zhèn)討生活。作為一個(gè)印第安人,她不能在白人的社會(huì)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卻反遭受白人的歧視與排擠,她郁郁不得志,于是在1981年(小說(shuō)的開(kāi)始)準(zhǔn)備搭乘汽車回到保留區(qū)。在等車的期間,她在酒館結(jié)識(shí)了一個(gè)白人男子,他答應(yīng)開(kāi)車送她回家,而在途中茹恩獨(dú)自下車,在暴雪中穿越山野林地。但她因在暴雪中迷失方向而未能回到家中,最后凍死在路旁。《愛(ài)之藥》以一個(gè)中年的印第安人回家的失敗為開(kāi)首,表明印第安人在追尋文化身份時(shí)會(huì)遇到很多磨難,甚至?xí)允《娼K。茹恩的死并沒(méi)有使家族第三代子孫們放棄追尋身份的歷程,相反,她的死為印第安的后輩們提供了回家的機(jī)會(huì):分散在保留區(qū)外的家族成員為參加茹恩的葬禮都回到了家中,分裂的家族又重新聚合在一起。
回家不僅是家族中年一輩人的選擇,印第安的年輕一代也選擇回家,重新回到印第安文化傳統(tǒng)中。小說(shuō)的第二篇,在大學(xué)讀書的艾伯丁開(kāi)車回到保留區(qū)參加阿姨茹恩的葬禮。在家里,她切身感受到親友們的傷痛以及家道的衰落。艾伯丁是小說(shuō)中的一個(gè)重要人物,雖然她有一半瑞典血統(tǒng),只能算得上四分之一齊佩瓦人,但她將自己認(rèn)定為印第安人,整個(gè)家族的故事因她的存在而被串聯(lián)起來(lái)。她從眾人對(duì)茹恩過(guò)往回憶中梳理出家族的歷史并重新認(rèn)識(shí)了印第安的文化傳統(tǒng)。她意識(shí)到過(guò)去(歷史)是構(gòu)成現(xiàn)在的基礎(chǔ),沒(méi)有過(guò)去就沒(méi)有現(xiàn)在;對(duì)于新一代的印第安人來(lái)說(shuō),追尋自己的文化身份、回歸印第安的文化傳統(tǒng),才能真正認(rèn)識(shí)自己,并在白人的世界中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想要在紛繁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印第安的傳統(tǒng)文化才是他們的最終選擇。
四、結(jié)語(yǔ)
《愛(ài)之藥》講述的是20世紀(jì)中期在美國(guó)《道斯法案》影響下的印第安齊佩瓦族人的生活經(jīng)歷。他們受到白人文化對(duì)其傳統(tǒng)文化的排擠和壓制,但他們并沒(méi)有因此而屈從于白人文化,而是在記憶中尋找歷史和印第安文化傳統(tǒng)的印跡;在兩種文化的碰撞與沖突中,他們選擇回歸到印第安的文化傳統(tǒng)中并追尋自己的文化身份。厄德里齊將自己的生活經(jīng)歷附加在小說(shuō)中的人物身上,透過(guò)這些處于社會(huì)邊緣的印第安人之口發(fā)出自己的呼聲:“吾乃源于此,亦永為吾屬”(HereIam,whereIoughttobe)[4],表明只有印第安的傳統(tǒng)才是自己永遠(yuǎn)的歸屬。但由于歷史的發(fā)展、環(huán)境的變遷及白人文化的多年浸染,印第安文化傳統(tǒng)也發(fā)生著轉(zhuǎn)化或改變。因而,當(dāng)代印第安人并不能在真正意義上回歸印第安的文化傳統(tǒng),他們?cè)谒季S方式等方面不自覺(jué)地受到白人文化的影響,厄德里齊在《愛(ài)之藥》的寫作上就受到主流文學(xué)的影響。所以,印第安人在堅(jiān)守傳統(tǒng)文化的同時(shí),也在不斷地豐富著本族裔的傳統(tǒng)文化。
參考文獻(xiàn):
[1]CarrollDThesubjectinquestion[M]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2:117
[2]ErdrichLLovemedicine[M]NewYork:HarperPerennial,1993:248
[3]OwensLErdrichandDorris''''smixedbloodsandmultiplenarratives[M]∥WongHDSLouiseErdrich''''slovemedicine:Acasebook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0:59
[4]ErdrichLWhereIoughttobe:Awriter''''ssenseofplace[J]NewYorkTimesBookReview,1985(1):23
[5]SawyerTSAssimilationversusselfidentity:AmodernNativeAmericanperspective[M]∥JohnRMContemporaryNativeAmericanaddressUtah:BrighamYoungUniversityPress,1976:203